【宾川时讯•文化周刊】故事里的村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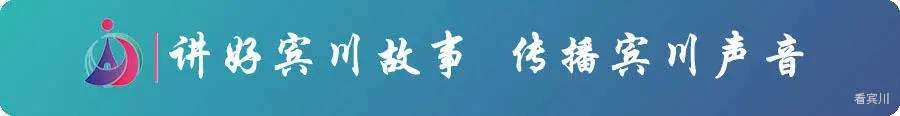




•张若恒•
拉乌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拉乌因故事而有魅力。
有幸参观了吴宗伯大大的农耕文化园,那里浓缩了一个村庄的故事。
拉乌躲在彝乡一个山卡卡里,距宾川县城和祥云县城都很远,属于两州三县的交界地,四面都是高山,中间有一条清澈的河流。独特的气候和自然环境封闭不了、也阻挡不了拉乌人民前进的步伐,先辈们选择走出去,形成了马帮文化;祖先们选择了自力更生,就有了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耕文化。在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许多农事都成为故事的时候,我们是选择遗忘还是铭记?吴宗伯大大的农耕文化园选择留住故事。

一部电话,一张布票,一个盐巴盆,一扇石磨,一双阿妹格,一件蓑衣......都有故事。断断续续的故事看似孤立连接起来就是一幅拉乌的风俗画,故事就这样慢慢展开。
之一:行路
拉乌通公路的时间很早,但是在很早以前整个拉乌就只有一辆拖拉机。听到车子的声音小孩子都会相约“走瞧车子去啦。”
看着展出的一块电子表,吴大大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电子表的故事:

在没有手表的年代人们都是看太阳,天亮出工,日落收工。天阴看不到太阳,人们就听赶马雀的叫声,路程远的赶马雀叫第一次收拾农具回家,路程近的赶马雀叫第二次时要赶快回家。
有一位姓李的叔叔进城买了一块电子表,从此人们出工收工不再看太阳。早晨,妇女催促男人“你看老李都出工了,你怕快点。”傍晚,男人劳动累了,对媳妇说:“老李都收工了,该回家啦。”有一次,天阴。旁边干劳动的看到老李扛着锄头回家也跟着回家,但回到家左等右等天还不黑。第二天早上出去干劳动时见到老李,问“昨天咋会那么早就收工?”“昨天肚子疼,回家吃药。”“啊!”大家随即大笑。听众也笑,吴大大没笑,他接着讲。
一天早晨,李叔叔起床看床头的表怎么没有数字,李叔叔买表时卖表的告诉他戴一段时间后什么也不出来是电子干啦。李叔叔心想要是有人问起时间怎么办?他穿好衣服、鞋子也不跟家人说就往米甸走去,这时早醒的鸟儿刚叫,天上还有稀疏的星星。三十几岁的李叔叔脚下生风,走四十几公里到米甸街给电子表换上五角钱的一粒电子,屁股没有落地就高兴的往回走,回到家刚好赶上早饭。
拉乌地处山区海拔高,冷,雨量充沛,湿气大。人们劳动时风里来雨里去的,造就了拉乌汉子喜欢喝酒的习惯,但在粮食匮乏的年代吃饱肚子都做不到,哪有多余的粮食酿酒。有一位姓周的爷爷极爱饮酒,凭票到供销社买的酒还不够周爷爷痛饮两顿。生产队有聪明的人想出了用松针、用蕨根酿酒,但一方面很不成功产量低得可怜,另一方面极为难喝,简直与“酒”扯不上关系。喜欢饮酒的人到医院打针闻到酒精的味道都会流口水。
那时周爷爷才四十来岁,实在想喝酒,忍无可忍,翻箱倒柜把压在箱子底的钱找出来,拿上一只能装十斤的酒桶就出门。周家奶奶一把拉住丈夫说:“你瞧瞧,脚上就一双阿妹格,走得到牛井呐?”周奶奶提出家里编好的五双阿妹格要周爷爷带上,又从楼上取来一捆稻草递给周爷爷,“路上边走边编阿妹格,不是你咋走得回来。”周爷爷沿着峨溪河逆流而上,硬是把奔腾的溪水走干,翻过最高的山梁随后就是一直下坡,到牛井单边就要走十来个小时。
吴大大喜欢饮酒这个关于酒的故事他平时给人讲过,现在故事进了农耕文化园。

之二:主人
听农耕文化园主人讲故事的同时,我总会忍不住插话问起他的故事,听他自己的故事我们可以感受到到祖国的发展,企业的壮大,一个企业优秀文化的积淀。
吴大大是宾川县农村商业银行的退休职工,退休后写了两本关于拉乌风土人情的书——《漫语峨溪》、《彝乡情韵》,之后又自己创建了拉乌农耕文化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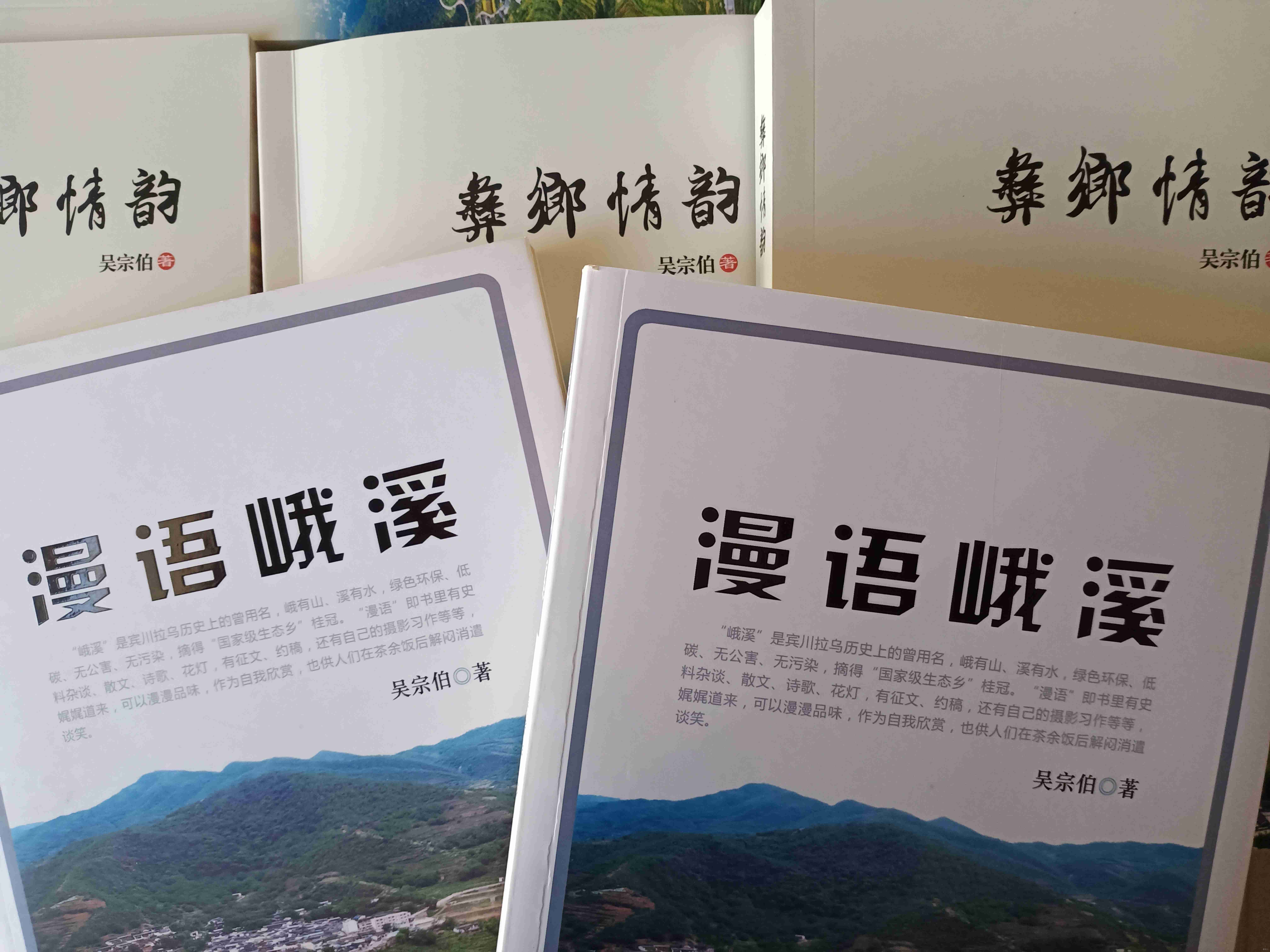
吴大大刚参加工作时候的单位叫农村信用社,属于农业银行的一个下属单位。当时他是拉乌乡上片四个村委会的负责人,金融服务包含片区居民的存取款,股金分红,所有生产队的集体资金,还包括在当地的一些国有企业的资金,如供销社、粮管所和当地教师的工资。
那个时候没有保安公司,库存资金的守护,大额资金的运送都要靠职工本人来完成。存款多时要送到古底,需要大额资金要到古底领取,路途中自己请一名信得过的村民陪同每天给一元二角的工资,安保器材就是腰上系着的柴刀。
单位没有一个像样的保险柜,库存现金的安全总是让人提心吊胆。到各村寨办理业务,要离开单位一两天,一个单位就他一个人总不可能把所有库存现金带在身上。吴大大有时把钱捆好埋在自己家里的谷堆里,有时藏在被子里,有时藏在房梁上,家里凡是能够藏钱的地方都藏过。更多的时候是在单位的墙角挖一个小坑把钱埋好再在上面扫上点垃圾放上扫帚铁铲。

到别的村委会给生产队送现金,出发前把现金用儿子用过的兜头布裹好勒在腰上。要到生产队就先到树林里把钱取下来,这个生产队需要多少钱点好放在衣服口袋里,一般会多出一点,让看到钱的人觉得他身上带的钱不多,不会心生歹念。每个生产队之间都是相隔很远的一段路程,出门办一次业务一天是回不来的,天黑了还要走一段山路,夜里走路一只手拿手电另一只手里攥着一块石头。晚上选择一家信得过的人家住宿,夜里一定要把门顶牢钱不离身合衣而眠。
以前村民手里没有钱,记得最少的一笔存款只有5元,这笔存款是分十次才取完。当时村里的信用社经常是处于亏损的状态,职工工资不高,有的职工嫌工资低主动辞职回家养牛养羊搞生产,但吴大大始终坚信企业一定会壮大,再说无论工资高低村民和集体都离不开家门口的这个金融机构,总要有人为乡亲和集体服务。

之三:山神
山川与人也是吴大大常讲的内容。
大年初二是一年中最适合外出的日子。在这一天,平时在一起放牧或者一起耕作的人们相约到平时种地或者经常放牧的地方做饭吃。虽然现在禁止野外用火,但是地边、核桃树下都有生产用房可供做饭使用。聚餐所用的食材是参与的人家你家拿一块肉我家拉一只鸡这样拼凑起来的。
开始做饭之前第一件事是祭山神。在山神树前插香压草纸,供奉上茶、米、油、盐、酒、肉等,所有供品都是生的,这一个环节叫做“领生”。等所有饭菜煮熟之后再把所有食材给山神供奉上一次,这一次叫做“回熟”,所有男女老少都到山神树前磕头,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牛羊肥壮,出门平安。

感觉山神酒足饭饱之后人们才开始摆席,在平整的空地上撒上一米宽长长的绿色松针作为餐桌,所有美食都摆到绿色长桌之后人们席地而坐开始吃肉喝酒。太阳偏西人们酒足饭饱,女人收拾好用具踏着夕阳归家。男人有的半醉有的大醉,此时路对于他们来说是长处走不完宽处不够走,只好相互搀扶着唱着山歌朝家的方向去,实在醉的家的方向都不知道。男人走一段路觉得脚软,把身上的羊皮挂丢在地上或躺或睡在上面对着山梁唱起了山歌,“砍柴莫砍葡萄藤,有女莫嫁赶马人......。”
好的故事父母会给孩子常常讲,一代一代的讲下去,就成了家风。一个村庄有一个村庄的故事,上一辈讲给下一辈听,这样讲下去就成了一个村庄的文化,这质朴的文化里有稻花的清香,有泥土的滋味,有风吹过森林的回响,有红杜鹃的浪漫与热情。

有些故事是我们这一代人听过,有些事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慢慢的也将成为故事。我们的孩子将会远行,村庄离他们渐行渐远,我愿他们的行囊中装着故事里的村庄,如同那一捧家乡的红土,那里承载着暖暖的温情。
作者/张若恒
编辑/杨宏毅
责编/杨宏毅
审稿/张进
终审/杨凤云
投稿邮箱/bcrntzx@163.com


网友评论文明上网,理性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