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川时讯·文化周刊】冬阳抹白



◎/李红文
冬日的萂村,阳光确乎是沉下来的。不像春日那样浮,夏日那样躁,秋日那样脆。它像窖藏了许多年的老酒,泼洒下来,不是光,倒像是黏稠的、微温的琥珀浆子,缓缓地,沉甸甸地,淌过枯草,漫过光秃的枝丫,最后凝滞在这片山坡的葡萄地里。天是高远的瓷青,一丝云也没有,干净得叫人心头也空落落的。风是有的,只是经过这里时,也仿佛被这沉静的阳光滤过一遍,失了棱角,只剩一缕清清冷冷的鼻息,拂在脸上,痒痒的。
 地是枯黄的。葡萄的叶子,夏日里曾是怎样肥腴的、绿得发乌的巴掌,哗啦啦地摇着一园的荫凉,如今都蜷缩了,干皱了,成了泥土上一片片褐色的、脆薄的蝉翼。轻轻一脚踩上去,便“咔嚓”一声,碎成齑粉,那声音细微得几乎听不见,却一直震到脚心里去。藤呢,脱尽了华服,便显出一种虬曲而倔强的本相来,铁黑色的筋络,一根根,一匝匝,紧紧地绞着,扭着,像沉睡的龙蛇,又像老人手背上暴凸的、盘结的血管。它们沉默地趴在支起的架子上,线条是硬的,冷的,在冬日稀薄的空气里,划出一道道瘦硬的、写意似的影子。
地是枯黄的。葡萄的叶子,夏日里曾是怎样肥腴的、绿得发乌的巴掌,哗啦啦地摇着一园的荫凉,如今都蜷缩了,干皱了,成了泥土上一片片褐色的、脆薄的蝉翼。轻轻一脚踩上去,便“咔嚓”一声,碎成齑粉,那声音细微得几乎听不见,却一直震到脚心里去。藤呢,脱尽了华服,便显出一种虬曲而倔强的本相来,铁黑色的筋络,一根根,一匝匝,紧紧地绞着,扭着,像沉睡的龙蛇,又像老人手背上暴凸的、盘结的血管。它们沉默地趴在支起的架子上,线条是硬的,冷的,在冬日稀薄的空气里,划出一道道瘦硬的、写意似的影子。
 妻就在不远处的另一行。她蹲着身子,藏青的袄子裹得紧紧的,头上包着网购的帽子,整个人便也像这土地上长出来的一株安静的植物。她做活细致,一手提着那盛了石灰浆的桶,一手拿着刷子,从那毛糙的、裂了缝的葡萄根茎部,由下往上,慢慢地,一圈一圈地抹上去。那石灰是昨夜用水新发的,此刻在盆里,是膏腴的、润泽的雪白,还微微地散着一点热气和石灰特有的、微呛的生气。刷子过处,那黑褐的、斑驳的老皮,便被这一抹皎洁的亮色覆盖了,像给一个历经风霜的老人,缓缓地戴上了一截崭新的、温暖的护颈。
妻就在不远处的另一行。她蹲着身子,藏青的袄子裹得紧紧的,头上包着网购的帽子,整个人便也像这土地上长出来的一株安静的植物。她做活细致,一手提着那盛了石灰浆的桶,一手拿着刷子,从那毛糙的、裂了缝的葡萄根茎部,由下往上,慢慢地,一圈一圈地抹上去。那石灰是昨夜用水新发的,此刻在盆里,是膏腴的、润泽的雪白,还微微地散着一点热气和石灰特有的、微呛的生气。刷子过处,那黑褐的、斑驳的老皮,便被这一抹皎洁的亮色覆盖了,像给一个历经风霜的老人,缓缓地戴上了一截崭新的、温暖的护颈。
我也蹲下来,学着她的样子。石灰浆触到树皮,是一种滞涩的、却又温驯的质感。那白色,起初是湿漉漉的,有些晃眼,不多时,水分被干冷的空气与粗糙的树皮吸了去,便凝成一种哑光的、粉扑扑的白,紧紧地熨帖在藤上。这活儿,静极了,也慢极了。世界里仿佛只剩下这“刷——刷——”的、单调而又丰腴的声响,和着阳光流淌的微响,以及自己胸腔里那均匀的、沉缓的搏动。
 做着做着,忽然想起《楚辞》里的句子来,虽不切题,那意境却幽幽地浮上心头:“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我们此刻,饮的怕不是坠露,是这满把清寂的冬阳;餐的也不是落英,是这泥土与朽叶混合的、微苦的芬芳罢。又仿佛不是我在涂抹,倒像是王摩诘在辋川的某处山坳里,对着他亲手栽种的辛夷坞,做着同样朴拙的事。只是他的辛夷花“纷纷开且落”,自开自谢,是绚烂的寂寞;而我们眼前的这些铁藤,却是将所有的生机,所有的甜润的梦,都严严实实地敛藏到那敷了白的根底下去,做着一个关于来年春天,关于紫玉璎珞的,沉甸甸的、黑白分明的梦。
做着做着,忽然想起《楚辞》里的句子来,虽不切题,那意境却幽幽地浮上心头:“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我们此刻,饮的怕不是坠露,是这满把清寂的冬阳;餐的也不是落英,是这泥土与朽叶混合的、微苦的芬芳罢。又仿佛不是我在涂抹,倒像是王摩诘在辋川的某处山坳里,对着他亲手栽种的辛夷坞,做着同样朴拙的事。只是他的辛夷花“纷纷开且落”,自开自谢,是绚烂的寂寞;而我们眼前的这些铁藤,却是将所有的生机,所有的甜润的梦,都严严实实地敛藏到那敷了白的根底下去,做着一个关于来年春天,关于紫玉璎珞的,沉甸甸的、黑白分明的梦。
思绪像藤蔓,一旦抽开,便收束不住。由这手中的白,忽地便跳到都市里那些刺目的光与色上去了。那惨白到令人心慌的灯红酒绿,打在每个人同样惨白而紧绷的脸上;那酒盏交错间,琥珀色的液体晃动着谄媚的、算计的流光;那霓虹招牌,将半边天都染成一种不真实的、浮动的紫红,像永远无法愈合的糜艳的伤口。那些话语,裹着蜜糖,内里却藏着针尖;那些笑容,灿若春花,转眼便能凋零成冰。在那里,人与人是藤,却是相互绞杀、争夺着每一寸阳光与养分的藤,藤上或许也结果,但那果子,常常是空心而酸涩的。
 往大理机场准备降落的飞机从头顶掠过,飞机的轰鸣刺破了乡村的宁静,也惊觉了我悸动的内心……
往大理机场准备降落的飞机从头顶掠过,飞机的轰鸣刺破了乡村的宁静,也惊觉了我悸动的内心……
“想什么呢?”妻的声音轻轻传来,将我飘远的思绪唤回。她不知何时已挪到我身边的一株藤下,正仰头看我,额上沁出些微的汗珠,在阳光下亮晶晶的。我摇摇头,笑了笑,没答话。有些思绪,像这地底藤的根,太深,太乱,挖出来,见了风,反而不美。她也不追问,只将瓦盆往我这边推了推,说:“这株老,缝子深,你手劲大,给它抹厚些。”
我便接了盆,更仔细地侍弄起来。这大约是最老的一株葡萄了,主干有孩儿臂粗,树皮皴裂得厉害,深深的沟壑里,积着经年的尘垢与风霜。我将刷子深深地探进去,让那洁白的浆子,一点点填满那些幽暗的缝隙。这感觉,竟像在为一尊古老的、沉默的佛塑,细细地敷上最后一道金身。又或者,像一个归乡的游子,用温热的手,去抚平母亲额上最深的、那一道为牵挂而生的皱纹。
 阳光静静地移着。我们俩,两袭深色的影子,便在这枯黄与洁白交织的园子里,缓慢地移动,像是时光棋盘上两颗最安分的棋子。额上渐渐也出了汗,背上暖烘烘的。这劳作,不激烈,不出声,却将身体里那些从都市带回的、僵硬的、冷冽的东西,一丝丝地,都熨帖了,融化了。忽然便懂得了陶渊明,他“种豆南山下”,草盛苗稀,或许未必真在意那收成;他所求的,怕就是这“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那一份身体力行的踏实,与“但使愿无违”的心魂安宁罢。
阳光静静地移着。我们俩,两袭深色的影子,便在这枯黄与洁白交织的园子里,缓慢地移动,像是时光棋盘上两颗最安分的棋子。额上渐渐也出了汗,背上暖烘烘的。这劳作,不激烈,不出声,却将身体里那些从都市带回的、僵硬的、冷冽的东西,一丝丝地,都熨帖了,融化了。忽然便懂得了陶渊明,他“种豆南山下”,草盛苗稀,或许未必真在意那收成;他所求的,怕就是这“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那一份身体力行的踏实,与“但使愿无违”的心魂安宁罢。
日头渐渐偏西,那瓷青的天宇,边缘被染上了一抹极淡的、温婉的妃色。风似乎也停息了,空气里那股石灰的生气,也仿佛被这暮色驯服,变得柔和起来。一大片的葡萄藤,从根起一尺来高的地方,都匀匀地敷上了一层粉白,齐齐整整的,在愈发柔长的光线里,竟像列队的、静穆的士卒,又像一群束紧了素白衣衫、等待着什么庄严仪式的老者。
明天还要继续。我和妻直起腰来,相视一笑,都没有说话。将沾满石灰的桶和刷子粗略涮了涮,那浊水携着一缕白,汩汩地流进葡萄地。我们并肩站着,回头看这一日的劳作。满园的铁色虬枝,因了腰间这一圈素白的点缀,忽然便有了精神,仿佛从一场深沉的、关于冬天的睡梦里,微微地醒了一点盹,透出了一点清峻的、内敛的秀气。
 远山如黛,一层叠着一层,淡下去,淡到最远处,便与那天边那抹妃色融在一处,分不清界限了。近处的村落,已次第亮起了三两盏昏黄的灯,那光是暖的,毛茸茸的,像是在这巨幅的、清冷的水墨画上,不经意滴落的几滴温润的淡黄颜料。
远山如黛,一层叠着一层,淡下去,淡到最远处,便与那天边那抹妃色融在一处,分不清界限了。近处的村落,已次第亮起了三两盏昏黄的灯,那光是暖的,毛茸茸的,像是在这巨幅的、清冷的水墨画上,不经意滴落的几滴温润的淡黄颜料。
下山的路,脚步是轻的。踩在松软的、满是落叶的土路上,几无声息。手里空了,心却满了。那都市的种种,此刻想来,竟像上辈子的事了,隔着一层毛玻璃,影影绰绰的,不再能刺伤人。身子里满是阳光晒透的暖,与劳作后微酸的舒泰。忽然觉得,我们抹在葡萄根上的,哪里只是石灰呢?那分明是我们自己,从浮世的喧嚣里,一点点刮下来的、渴望沉静与洁白的念想;是我们递给这沉默土地的一份笨拙的、请求收留的投名状。
 这冬日的涂抹,大约也算一种“归根”罢。不是落叶归于泥土的那种悲壮的归根,而是将一颗在红尘里扑腾得满是尘埃的心,暂且安放到这最朴素、最坚实的劳作里,像藤将所有的力气,都沉潜到根,去贴近那片生它养它的、温热的地母的胸膛。
这冬日的涂抹,大约也算一种“归根”罢。不是落叶归于泥土的那种悲壮的归根,而是将一颗在红尘里扑腾得满是尘埃的心,暂且安放到这最朴素、最坚实的劳作里,像藤将所有的力气,都沉潜到根,去贴近那片生它养它的、温热的地母的胸膛。
回到小小的院门前,妻轻声哼起一支无字的、古老的调子。我推开门,一股带着柴火气的暖意,扑面而来。
图文/李红文
编辑/杨宏毅
责编/杨宏毅
审稿/张 进
终审/杨凤云
投稿邮箱/bcrmtzx@163.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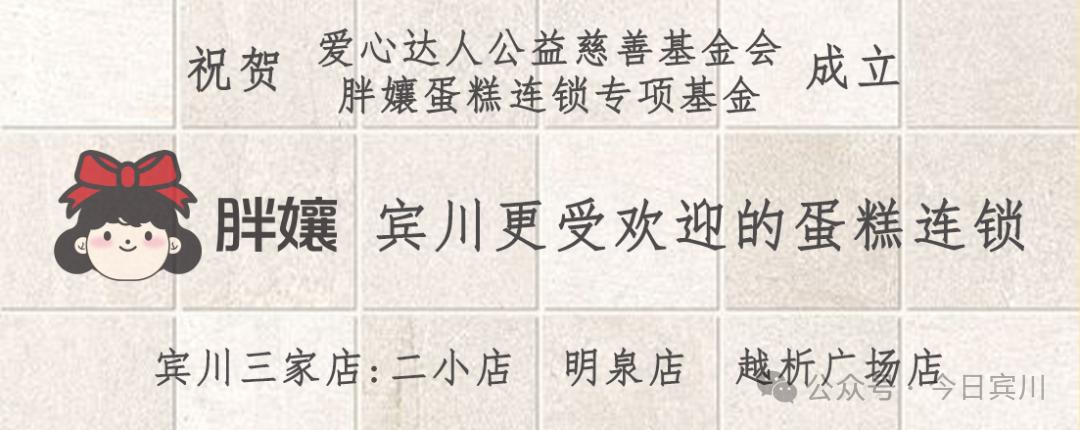



网友评论文明上网,理性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