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川时讯•文化周刊】挖茯苓 捡菌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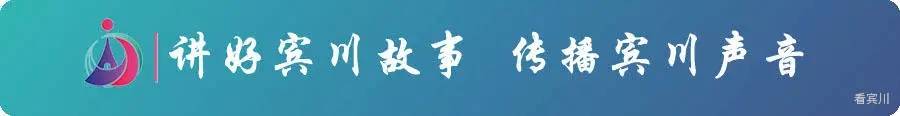




挖茯苓捡菌子
•丁 强•
读小学五年级暑假的一天晚上,“哗啦哗啦……”下了一夜的雨,天要亮的时候,雨终于停了。这是上山找菌子的最佳日子,我穿上塑料凉鞋,戴上篾帽,背上竹篮,篮子里装上一块塑料雨布,向汉邑村背后的塔拉摩大箐走去。

挖茯苓捡菌子,这是我儿时找菌子的常态,也是儿时的美好记忆。顺带捡鸡枞,也是常有的事。
我的家乡在古底汉邑村,小时候,并知道云南是动物王国、植物王国,只知道古底是“野生菌王国”,一到雨季,村背后的山上每座山都会出菌子,就连麻栎林里也有。

我们村能吃的菌子种类很多,最好的是香菌(香菇、蘑菇),只有塔拉摩大箐的原始森林里才找得到。其次是鸡枞,大坪地、南山坡、包谷地里都会出。再其次是青头菌、扫把菌、奶浆菌、铜绿菌,最差的就是山奔头(牛肝菌)了,我小的时候,根本看不起吃,看见了就一脚踢飞,能踢多远踢多远。

每到夏末初秋雨季来临,一场大雨过后,香菌、鸡枞、青头菌、扫把菌、牛肝菌就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头天晚上大雨过后,第二天天蒙蒙亮,我就走出家门,沿着村子背后的小路向塔拉摩大箐走去。走过麻栎林,走过大坪地,来到蘑菇房(地名,有土墙痕迹),走进大箐,就算是正式开始找香菌了。我在参天大树下、杂木树丛里寻找到栎树枯树桩、枯树枝,然后再在枯树桩、枯树枝上寻找香菌。运气好的时候,从蘑菇房开始就能找到香菌,黄白色的帽子、黄褐色的菌杆长在枯树桩、枯树枝上,总是让我欣喜若狂,即使身边没有任何人,也要快速、小心翼翼地把香菌采下来,轻轻放进竹篮里,生怕被别人“抢走”。一数,有十几朵,在竹篮底部铺了一层。用塑料布盖上香菌,继续向大箐深处、高处走去,我知道香菌最多的地方在“石岩子”(地名)。那时候,没有手机,当然也就没有手机定位可以导航,而要准确无误地找到出香菌的地方,全凭记忆。这个隐秘的地点就在“石岩子”对门塔拉摩大箐上方一条山箐两边。这里箐水悠悠,树木高大茂密,遮天蔽日,晴天白日都能看见星星。这里栎树较多,暴雨过后,菌子“爬满”枯树桩、枯树枝,让人目不暇接。我高兴得大叫:“哇,今天运气太好了,到处都是香菌!”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开始采香菌为好。我在山坡上香菌最密集的土坑里站稳,生怕踩到香菌,防止塑料凉鞋打滑跌倒压坏香菌,时而弯下腰俯身在枯树枝上采香菌,时而抬起头挺直腰板在枯树桩上采香菌。采下一朵放进竹篮里,接着采第二朵,直到把一片香菌采完,只留下刚冒出米渣大一点的小香菌不采,留着它们长大点再来采。

我把斜跨在背上的竹篮轻轻放在身前,一屁股坐在一根刚采过香菌的树杆上,看看篮子满了没有,顺便休息一下。突然,山头传来叽叽喳喳的鸟叫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原来是一群长着黑白相间羽毛的竹鸡,当我们四目相对的时候,大家都被吓了一跳。竹鸡向矮树丛中飞奔,我不管篮子向山坡上追去,结果只有两条腿的我,没有追上长着翅膀的竹鸡,空手而归。这有点像小学课本里的《小猴子下山》掰包谷,到头来什么也没有得到。我及时制止了自己的错误,不再追赶,连爬带梭来到刚刚采香菌的地方。谢天谢地,篮子还在,香菌还在,我背起装满香菌的竹篮回到家。

一朵香菌、鸡枞、青头菌、牛肝菌基本是由菌杆、菌帽组成,我们把菌杆叫菌杆杆,形象地把还没有完全打开的菌帽叫“箍箍”。“箍箍”是菌子最好清洗、最好吃的部位,也是最有营养的部位。最好的香菌、菌子是“箍箍”还套在菌杆上,就像伞没有打开的样子。我把最好的香菌用竹签一朵一朵串起来,圈成一个香菌圆圈拿到古底街上卖,卖到的钱开学后拿来做书学费;“箍箍”已经打开、卖相差的香菌,洗干净后交给父亲,用火腿、鸡蛋炒吃。用锅铲铲起来时,故意留一点,舀一大瓢清水倒在铁锅里成了两个菜:一个火腿鸡蛋炒香菌,一个火腿鸡蛋香菌汤,都好吃。用来泡包谷面面饭,菜不好时只咽得下一钵头,用火腿鸡蛋香菌汤泡包谷面面饭吃,可以甩下三钵头。缺点是费饭。

那时候,我们汉邑村山上到处都出菌子,牛肝菌叫山奔头,分黑山奔头、黄山奔头,麻栎林里就有,但我们都看不上吃。最喜欢吃的当然是香菌,其次是鸡枞,再不济也要吃青头菌、扫把菌。其实,青头菌也好吃,炒吃、煮汤都可以,要是加点火腿就更好吃,关键是安全,从来没有中过毒。

我上小学时,暑假的主要家务是上山放羊顺带找菌子。放羊的主要地方是汉邑村下队王桥平地山、梭木头山、白杨条山,上队的大平地、老梅树、磨刀石箐、红土坡山,太阳山。一起放羊的小伙伴有时背一只竹篮,有时不背、打空身。看见鸡枞、箐头菌、扫把菌就捡来带回家。看见奶浆菌,就捡起来抹抹上面的泥土、灰尘,送进嘴巴里生吃。有时还会带点盐巴,除了喂羊,也拿来烧菌子吃。下雨天气冷,就烧一笼火,一边向火一边烧菌子,差不多要烧熟时,撒上一点盐。然后用树枝把菌子从火堆里扒出来,稍冷一点,就用手去抓。烫,没关系,把菌子左手颠到右手,右手再颠到左手,反反复复四五下就不烫了。撕一大块烧得黄生生、冒着汁水的菌子下来,塞进嘴里,香,好吃!吃五六朵菌子,也就饱了。热、口渴,用树枝把火打灭,到有山箐水井的地方,喝一饱山泉水,找羊赶下山。淌过磨刀石箐,路边有很多椭圆形的菌子,有鸡蛋那么大,我们叫“牛眼睛”。要开谢的“牛眼睛”叫“马屁泡”,外皮面包裹着菌孢粉,用力砸在地上、树丛里,立马会像炸弹一样炸开,腾起一团黄烟。羊走在前面,小伙伴们走在后面,嬉戏打闹,“马屁泡”就是最好的武器,打在潮湿的衣服上,中弹者马上就“挂彩”,衣服上立刻出现一大块黄斑。除了颜色难看,并不会伤人,只是图好玩。

上初中以后,有点憨力气了,就跟在村里的大人屁股后面去山上挖茯苓,挣书学费,找菌子不再是主业,而是变成了“不务正业”。找菌子也悄然变成了捡菌子,看见就捡,看不见也不去刻意去找,碰着好的菌子就捡起来装进竹篮里背回家。
为了挖到茯苓,我们几乎走遍了古底的每一座会结茯苓的山,就连拉乌乡碧鸡庄背后的大山也去过。走的山多了,什么样的苦都吃过,长大后遇到再难的事,也不觉得有多难。挖茯苓的次数多了,乐趣也就多了。正当口渴难耐时,眼前突然就会出现一蓬白里透红、熟透了的杨梅,用双手接二连三摘下来,放进嘴里,一含就化,酸甜可口,是解渴最佳免费水果。

挖茯苓巧遇鸡枞也是常有的事,有时鸡枞就长在木香桩桩边,在开挖茯苓前先一朵一朵拔完鸡枞,才开始挖茯苓。有时挖着挖着突然挖到白蚁窝,白蚁乱跑,一抬头才看见鸡枞就在锄头前,再挖一锄头,就会把鸡枞挖个稀潖烂。赶紧连刨带挖,一朵一朵拔完鸡枞,再挖茯苓。如果运气好,既捡到了鸡枞,又挖到了一两个大茯苓,那就太高兴了。回家路上一路美滋滋盘算:“今天没白跑山路,不仅挖到茯苓有钱花,还有好吃的鸡枞。”这就是古底俗语“挑水洗带菜,两头不耽误。”
这样的好事,我在汉邑村太阳山上碰到过,在古底牛角山、石灰窑箐头也碰到过。三四十年过去,这些美好记忆时常重现在梦里、浮现在眼前,有时自己都把自己感动得想哭,笑醒……

我高中毕业后知道,牛肝菌也是好东西,城里人爱吃,南华是滇西菌子集散地,菌子从这里运往昆明、全国各地。后来在昆明定居了,知道哪些菌子能吃、好吃,哪些菌子不能吃,对曾经看见就一脚踢飞的牛肝菌另眼相看,也会炒着吃了。但见手青从来不吃,怕中毒!

近期,全国都在下雨,又到了云南找菌子、吃菌子的季节。我从宾川朋友口中得知:平川地区雨下透了,可以找菌子、吃菌子了,而且可以快递到昆明、全国各地。
想吃家乡的菌子了!
作者/丁 强
编辑配图/杨宏毅
审稿/吴洪彪
终审/杨凤云
茯苓图片来自网络
投稿邮箱/bcrmtzx@163.com


网友评论文明上网,理性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