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川时讯•文化周刊】木香坪(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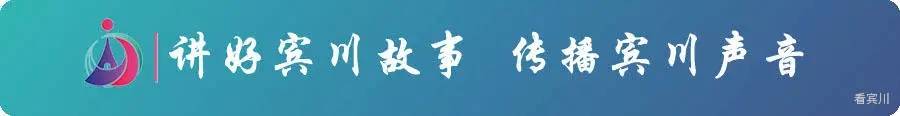



•张橙子•
木香坪是宾川海拔最高的地方。有多高? 3320米!也就是说,这木香坪的山峰还比鸡足山要高70多米。
不过,木香坪之所以著名,并不是仅仅因为海拔。
去年10月的一天,我们开始了计划中的木香坪之旅。同行的是几个文友。早上七点,天微亮,我们就驱车出发了。多云间晴天气,秋日的鸡足山的早晨,一束束清冽的空气不时撞入车窗,让人感到特别的惬意。一路上,有一些小鸟小兽的身影出现在景区的路上,我们谨慎地行使,希望不要对它们造成惊扰或伤害。树林深处,隐约的有传说中的念佛鸟的叫声传来,使整个山林显得更加清幽。路两侧,一排排高大苍翠的树木簇拥而立。而路的正上方的空间时不时地将鸡足山的巍峨与博大展现在眼前,让人陡升朝圣的心绪。是的,越接近鸡足山的腹地,就会越有“梵钟声彻三千界”的感念。

车行半小时,到了游览车上站的侧面,一条冷寂的土路与主路相连,指路牌上写着“放光寺”三个字。我们驱车拐进了土路,再行约2公里,就到了放光寺。放光寺是鸡足山八大寺之一,位于鸡足山南面、华首门的正下方,正所谓“处鸡足山胸臆之要穴,‘诸刹皆在山之肩背,而放光独当胸臆之穴’”。文献记载,放光寺始建于明朝嘉靖二十五年(1546),由僧人圆惺和弃官回乡的大理人李元阳创建。万历年间曾奉御赐,藏经于藏经阁,后倾颓。崇祯、康熙年间两次重修。之所以命名放光寺,是因为这里常现殊胜光相,如李元阳所述:“石门之下(放光寺),时见光瑞,或圆相,或摄身,与五台峨眉大都相似,余(与僧圆惺)即其地建创精蓝,因字之曰放光焉。”(李元阳《放光寺记》)。我们到达放光寺,就见几处庙宇、僧舍、客堂和一个中间大、两端小的弧形水池铺排在不同高度的台地上。紧靠危崖处,一座崭新的巨大庙宇拔地而起,金碧辉煌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庙宇为三层,高约20余米,最显眼的是那些柱子,都是二人不能围抱的直径,且都是层与层间不间断的通梢用法。我惊叹于庙宇的宏伟气势和人类的巨大力量。

我们停好车,准备上山。九点一刻,我们沿着一条小路走进了放光寺西侧的原始森林。小路腐叶铺陈、石子零乱,边往深处延伸,边抬升高度。行不多远,体力稍逊的人就开始有些喘息。我们放慢了脚步。由于各人的体能不一样,我们的队伍越拉越长。走着走着,身边的森林越来越茂密,渐渐地就隐藏了我们的行踪。
走了1公里左右,翻过了一个山脊,一阵水声从不远处传来。眼前有一块比较大的开阔地,地上面有许多罗汉塔。知情的杨老师告诉我们,这里是放光寺的塔院,是埋葬已故僧人的。

我们在塔院里观看那些僧塔,有大的,也有小的;有年深日久的,也有稍新一点的。大约有十几二十几尊吧。我简约地参观了几座大的,看了看铭文,猜测着里面是什么样的高僧在此坐化。这时,就见一位穿着厚实僧袍的和尚在不远处的一座小屋前跟我们打招呼——原来他是常年在此修行并守护塔院的僧人,看上去体型壮硕、正值中年的样子。
中年僧人忙着给我们烧了开水,为我们沏茶。我看着那僧人,默想着他一天到晚、特别是夜深人静后的生活起居,不禁有些悲戚。是的,当我们沉迷于网购、乐享着高铁或是飞机带来的便捷的时候,竟然有人能够抛却人间的浮华来到这世外之地,这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啊!
我喝着山泉水沏出的茶,感觉一丝惬意涌上心头。忽然觉得,我们每天呆在城里,喝着经过处理的水,几乎已经喝不出水的原生味道,也许这对于局外人来讲,才真的是一种悲哀呢!

茶过三巡。我们继续朝山上走。离开塔院约三百米,我们就进入了一条叫做桃花箐的山谷。山谷里没有桃花,十月也不见有桃子。仔细找了一下,也不见桃树,就觉得这桃花箐也真是徒有虚名,也不知这样取名是谁的主意。
桃花箐很深,也很陡,一些蜿蜒崎岖的小路就在箐的两侧迂回攀升。路上有一些新新旧旧的蹄痕和骡马的粪便,看得出这地方隔三差五是有人前来探寻的。路边上是一些树木,有云南松、水冬瓜、映山红、黄栎树,也有许多不知名的杂木树,树上挂着苔藓或灵芝。有不少枯枝经不住岁月的磨折与摧残,落到了潮湿的地面上,身上又长出了青苔或蘑菇,开始了又一次的轮回。
沿着山谷逶迤前行。小水流在沟谷里流淌,大约是山势太陡的缘故,水流得有些慌不择路,山路上也遍地是水坑水洼,黝黑的树桩旁长着千姿百态的菌子,不时为我们提供着新鲜感。我们走得小心翼翼,一方面怕把鞋子弄湿了穿着不舒服,另一方面也怕崴脚、跌跤。这样,我们的队伍拉得更长了。

经过40多分钟的路程,我们到达了桃花箐垭口。垭口西面有一片开阔地,中间是草甸,边缘上却长着茂密的高草,看着甚为养眼。在垭口处,一个两米多高的玛尼堆立在路边,可知这里也曾有藏地僧人或信众活动,让人想起磕长头的情景。据传,在大理国时期,曾经有一条从海东、挖色出发的朝山古道向北经木香坪到鸡足山,而我们目前走的,就是这条古道的其中一段。时至今日,大理海东挖色一带的白族同胞和藏地徒步而来的朝圣者有的仍然会走这条路。而桃花箐垭口则是去金顶和祝圣寺两大寺庙的分路点。
从垭口开始,山路变得有陡有缓,而且路上也不再有水迹,山上则多为灌木或草坡,眼前就空阔多了。路边上还不时有一些颜色鲜艳的小花、玲珑剔透的山果吸引着我们的目光。看到景色不错,有人哼起了小曲。

我也觉得惬意,摘了片树叶吹起来。不过,由于多年不吹叶子了,中气不足,技艺退化,曲子总是中断。有个摄影师见我吹得有趣,竖起微录机录了一段。同伴中也有人对花花草草、树木种类或是草药感兴趣的,就停下来看啊看、嗅呀嗅的。
小路在山坡上绕来绕去。从桃花箐垭口到白王城山约有四公里,中间一段是在山脊上走,向东可看见尚缭绕着云雾的母猪山,向西则可以看到洱海的一小部分。山脊上树木变得稀疏,山坡上土层也薄,只有一些低矮的刺栎树、小杜鹃等能够生长。许多人又停下来拍照。此时约莫11点钟,东面山峦的景色不错,有几个画一样的村庄影影绰绰地镶嵌在碧绿的山间,估计长焦镜下画面会好。不过,在前往白王城山的后半程,路左侧就是悬崖,又是那种高低不平的石头路,有几处也很陡峭,所以大家都走得比较谨慎。

白王城山是一座小山峰,在一列准东西向的山岭的北面,那山岭地势东高西低,而山岭的最高处就是3300米海拔的木香坪梁子,它其实是在被称为木香坪的那个草甸的东北面,跟草甸还有一段距离。
越过白王城山时,离我们出发的放光寺约有八九公里了。我们从山岭的西段向南走。就在大家都感觉到有些疲惫的时候,我们到达了一个小山垭口。在山梁上向南望去,不远处,一个平缓的大草甸尽收眼底;向西看,则能看见洱海的一片很大的水域。站在山梁上,小风轻轻地吹着我们的脸颊,让人感到心旷神怡。

木香坪草甸约六七平方公里的样子,它三面环山,西面则相对低矮,是一个高山草甸,平时有来自大理市挖色镇境内的人在这里放牧牛马,也有一些驴友前来探访。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一些地段上的草色已略显枯黄,而靠近山谷的地方却依然芳草萋萋,有五六群约百数头牛马在草甸上徜徉,几个闲云野鹤似的牧人在闲逛,身边跟着一两只小狗,看上去十分散漫悠然。细看脚下的那些野草,中间竟然夹杂着地丁、龙胆、白芨、青蒿、仙鹤草之类的草药,一些还开着些紫的、黄的小花。还有一种叶面宽阔肥厚的植物,赶马的大哥说那是一种叫云木香的中药。我看看那些靠近水沟的地段,竟然到处都有那种植物的身影。我想,如果那种植物就是所谓的云木香,那木香坪这个地名估计就跟它有关吧!据说木香具有行气化滞、疏肝健胃的功效,是农家必备的常用药,所以会不会是有些人到这里挖过药,发现这里木香多,就把这里叫做木香坪呢!只不过,大家都说不出所以然来。我能确定的是,这里的草木生长良好,又没有农药化肥的污染,对于牛马来说,绝对是优质纯天然的食物了!
我们驻足给牛马拍照,牛马们张望着我们。也有一些牛像是吃饱了,静静地卧在草地上假寐,嘴里反刍着。再看看这水草丰茂的草场,牛马们悠闲地来来去去,吃着天底下最可口的草料,我觉得这里的牛马简直就是世上最幸福的牲畜,比起在鸡足山赶脚驮货或是被圈起来圈养的同类,不知要舒服几千倍。

从一些关于木香坪的网文书写的情况来看,有一些驴友从洱海东面来,有一些从鸡足山方向来,也有一部分则从鸡足山对面的白草龙村方向来。不过,我猜应该还有一些人就来自附近的山村。因为草甸上有许多条通往不同方向的小路。草甸上有各种人畜活动的痕迹,让人觉得这里其实并非化外之地。这些年由于大家手里都有了一些闲钱,一些人又比较有空,交通条件也方便了许多,所以,很多人置备了长枪短炮的摄影器材,最不济的也起码有个像素不错的手机,几乎任何一个风景殊胜的地方都有人专程前来探访,再加上现在通讯发达,看见一个景、一株树、一朵花都忘不了要发个朋友圈,所以,但凡有点风光的地方都被传出了名气。木香坪也不例外。根据一些人发出来的图文,据说附近还有万亩连片的杜鹃林。但是,在我们走过的区域,除了看见过不多的几株杜鹃树外,并不曾见过连片的。当然,目前并不是花期,所以也不觉得遗憾。

我们在草甸下方的小沟旁坐下来休息,吃着素食的烙饼和食物。每个人都感受到了被关怀的熨帖。在木香坪这样的天然大氧吧里,不带荤腥的素食吃着也非常有味,这种味道是粮食自带的,在特定的环境里被我们的味蕾捕捉,像是一种久远的回归。

我们逗留的地方不远处有一片水洼,附近有一个水塘和两口小井。水塘呈半圆形,水深盈尺,边缘用石块砌筑而成;井则是民间常见的那种,都筑了一个水泥井圈,不细看的话,也不知何人所修。不过,仔细一看就会发现,其中一口的井圈上竟然还有铭文。我首先看到的是内环处的一圈英文,大意是鸡足莲花山大师父释某某;落款处则为中文繁体字,曰:岁次壬辰年佛历3039年,公元2012年敬造。原来,这是一处由鸡足山僧人修建的水源设施。

突然,我们被水井附近的景色吸引了注意力。因为,那水井以上是一条小沟,沟里流着弱弱的溪水,而小溪旁则正盛开着鲜艳的红蓼花,一朵朵、一丛丛,看着干净而新鲜。大家都被这种进入冷凉气候却依然开放的小花给迷住了,纷纷摆出各种姿势来照相。
我们就这样在草甸上流连,看尽了寂静中生长着的花草。然后,我们收拾起所有的弃物带走,不给这片净土般的草甸留下垃圾。

返程时,我们选择了另一条路走出草甸。经过一段很陡的石头裸露的山坡,我们再次攀上了木香坪梁子。这回走的是梁子的中段,是梁子的最高峰。这是长圆形的山丘,山两侧都有一些灌木,山脊上则光溜溜的。我们在山梁上回望,木香坪草甸犹如一块巨大的毡毯,静卧在群山之间;远处的洱海则苍茫一片。再看看鸡足山的方向,高高的楞严塔仿佛就在眼前。一种多年夙愿一朝实现的感慨突然降临。
看着草甸上徜徉的牛马,我们情不自禁地学着牛叫。有趣的是,竟然有几头牛有了反应,“哞、哞”地回应着。
我们在山梁上以鸡足山为背景合影留念,同时也各自照了不少照片。就着这里还有一点点手机信号,大家都尝试着发了朋友圈。只是,没成功。

返程的路都是下坡,一路上,有人发现山坡上有不少龙胆草,就采了一些。大家走得非常轻快。不过,要走完这来去约二十几公里的路程,脚力、体能、心脏都还是经受了考验的。想想这一路的行程,我看到了美丽的风景,也体验到了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耐力的感觉,更体会到了在庸常的环境中无法得到的愉悦,就跟那些去过雨崩或藏地的人一样,正所谓“身体下地狱,眼睛上天堂,灵魂归四方”了!
待我们走完了这条险峻的山路回到放光寺的时候已是下午5点多钟。夕阳里,我忽然觉得,木香坪风景固然很好,但由于这一路上没有补给的地方,大多路段也没有手机信号,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无人带路或是身体状况不太好的人,还是不去的好。

而且,木香坪有茂密的森林,旖旎的草甸,清新的空气,但它经不起一个烟头的放纵。与其一窝蜂地涌去践踏,不如让它处子般地存在于我们的梦境之中吧!
作者/张橙子
编辑/杨宏毅
责编/杨宏毅
审稿/吴洪彪
终审/杨凤云
投稿邮箱/bcrmtzx@163.com


网友评论文明上网,理性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