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川时讯·人文宾川】排营小村岩棚(附万人冢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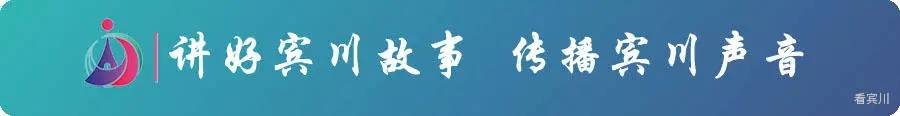



排营小村岩棚
(附万人冢碑文)
·申研墨·
多年前打算集合一下过往所有有关家乡的一系列小文章,进行一番系统整理,然后出一本小书——《云南小村排营小志》。一个村邻偶然一起闲聊,于是讨论起排营坝子究竟是先有排营还是先有岩棚!他认为排营三滴水从令字山前后左右涌出,流经排营村,然后到了岩棚汇聚成横穿排营坝子的横溪(现岩棚大河,《雍正宾川州志》桥梁里记载有:龙津桥,在排栅营东,跨横溪。),水流裹挟而下的泥沙在岩棚附近形成肥沃的土地,于是牛井、宾居一带的古人才顺着水流寻着水源来到排营坝子,并在那土地肥沃的岩棚开启了新生活,所以排营坝子最先有的村落就是岩棚。但是我并不赞同。既然古人为了寻找源头顺着流水来了,那么就一定会继续寻踪到排营或者甸头、西村,因为汇聚成岩棚大河的“丹凤朝阳三滴水”的三滴水的源头都在排营坝子的最南端,都在“犀牛望月令字山”的令字山里面,而另一股稍大的的水源头则在甸头滴水山山箐里,最不济的一股也是由西村老太箐流出来,所以还有老人在解释过年时排营坝子每个村耍的龙的颜色时,说是因为排营、甸头、西村处在水源头上,所用的水清澈无比,所以就耍青龙、白龙,而岩棚、四家在水的下游,那水已经浑浊,才耍黑龙、红龙。当然这个解释并不正确,正确的解释应该是根据村子所处的方位而定的每个村的龙的颜色,就与大理古城内的五龙井一个道理。但这并不影响我认为排营坝子最先有的村子不是岩棚而是排营的推论。
岩棚村名本来不是这两个字,在明朝万历时期叫“莱篷”,在《雍正宾川州志》里叫崖棚,后来不知什么时期又被叫着“岩漰”,到解放后才定下了“岩棚”这两个字,白族话则叫“e bo(都是去声)”,现在有三百八十多户,一千四百人左右。村子沿着东西走向的岩棚山一串儿排开,民居依着岩棚山脚分布,就像一根粗线条,去鸡足山的旅游路岩花公路就在村子后面,掐头去尾,好多路段都与岩棚村成平行线的关系。岩棚山多青石(石灰岩),从排营一眼望去,感觉就像尽是石头一样,所以在一些碑里被叫着岩山。岩棚村东边到达龙津桥附近 ,西边与四家村交汇,凭眼力已经无法区别开两个村,但对于岩棚人与四家村人他们却很明确的知道自己是哪个村的。

岩棚村原来包含拱桥村,是排营下辖的第二大自然村,本来只比排营村少四五十户,但现在有八十多户人家的拱桥村好像已经有了自己的自然村村长,在村委会的公示栏上已经单独列了出去,所以感觉他比西村都少了十几户人家,从人口上来看,感觉沦落为了排营坝子第三大的村子,但作为排营坝子的人却自然还一直知道拱桥村与它的关系,所以事实上它还是排营第二大村。
岩棚整个村子都是白族,当然娶亲招赘进去的自然有着汉族、傈僳、纳西族等各种民族,但毕竟很少,不过百分之零点几而已。岩棚村里张姓最多,其次是杨姓,然后还有赵陈李吴蒋等杂姓。

在我们白族聚居的地方,一般一个坝子只有一个本主老爷,但我们排营坝子却有两个本主老爷。一个是整个坝子都敬奉的天神大黑本主,一个是只有岩棚才接送的斩蛇英雄粱朝选本主。岩棚村有一个口耳相传的故事,说是在明万历年间,邓川北极村一个叫粱朝选的秀才带着弟弟粱朝纲想要上京去考状元,他们就到牟川(排营)来约一个同学一起做伴。他弟兄二人离开邓川,沿着洱海前行,经过双廊,经过挖色,走出萂村坝子到了排营萂村交界的磨房箐时,突然出现一个老人拦住了他们,郑重其事的告诫说:前面莱篷村山里面有一条大蛇,能囫囵吞下牛马,并且经常吃人,村民深受其害,已经搬迁了不少。劝阻他俩不要继续往前走,更不要经过莱篷村,不然如果遇到了那条大蛇,他兄弟二人都将会性命不保。兄弟二人考虑了一会还是继续前进了,要到牟川,只有经过莱篷村村心的那条路好走。不过他兄弟二人运气不错,居然没有遇到大蛇。在牟川同窗家小住的时候听到人们谈论起那条大蛇,谈起莱篷村民的悲惨境况,梁朝选久久不能入睡,想了好久,他对弟弟说:我们上京求取功名,为的就是当官,然后为人民做主,救人民出水火,如今莱篷村民已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不去救,那么我们去考取功名还有什么意义!不如我们弟兄一起去把那大蛇杀了,挽救莱篷村的人民,这比考取功名才去救助百姓简单得多啊!粱朝选的这番话真的很感动人,与现在那些本来只该卖红薯却占据庙堂的人比起来,显得更是伟岸。弟弟听了哥哥的话,也很赞成。于是他们兄弟二人找到铁匠,打造了许多兵刃,然后在全身上下捆绑了许多刀剑,手里还拿了一把大砍刀。准备好了后,兄弟二人主动到了莱篷后面山里,四处去寻找那条大蛇。大蛇出来了,真的很大,比水桶还粗,长几十米,眼睛有碗那么大,吞吐的蛇信就像一根猩红的蛇矛。粱朝纲因为岁数小,看到那么大的蛇后,直接吓得手脚酸软,不能动弹。粱朝选却英勇无比的挥舞着大刀扑了过去。二者搏斗了好一会,大蛇毕竟厉害,把粱朝选连人带刀一口吞了下去。粱朝选全身都绑缚了锋利的刀剑,被吞进去后大蛇就疼得受不了,在大山上横冲直撞上下翻滚,压倒树木,撞碎巨石,最后终于不在动弹,完全死了。痛失亲哥,粱朝纲蹲在大蛇尸身旁边放声大哭。莱篷村残存的居民早被山上的搏斗惊动,匆忙赶到了现场,然后一起剖开蛇腹,把粱朝选从蛇肚子里找了出来,可惜粱朝选早已经没了呼吸。于是安排人赶到邓川,去通知粱夫人。粱夫人来到莱篷,看到丈夫尸身,痛哭一场后也撞在旁边的山岩上,以身殉情。莱篷村的村民很感激,也很感动,就在安葬他们夫妇的岩山之麓修建了一座庙宇,塑了他们夫妇的像,把他们尊为了本主老爷,尊号为“道厚忠流表高景帝”。并在每年正月十一接整个坝子的大本主天神大黑的时候,也把他接了去供在天神大黑本主身边一起受拜祭。平常八下也常有居民去烧香磕头。不知多少年后,陆续搬回来的人们在山上砍荆棘开山地时,发现荒野之中的累累白骨,就把它们都收拾到一起,埋在粱本主庙一侧,更是把村名都改成了岩漰,到1962年,在新中国的领导下,人们的生活蒸蒸日上,于是感怀本主老爷的恩德,重修粱本主庙,就把这个口耳相传的古老故事刻在了庙里面。并作词曰:岩山苍苍,湔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又诗曰:四面青山景色幽,牛山当案水环流;笔峰为屏江缠绕,门迎绿野喜盈丰;令山高拱案犀牛,梁墓安落凤点头,大道环抱锦作带,地灵人杰世英风;庙建凤冠凤朝阳,左旗右鼓滴水三,墓枕岩山观音阁,北陌东阡风景佳,彩凤含书抱乡村,双株翠柏绕瑶阶;遥瞻栖树荫庙宇,青狮滚绣带子归。

现本主庙就在岩棚观音阁的下面,在靠近四家村的这一边,已经处在村子的内部,本主庙大院里现在还合并进去了一所文昌宫。
但莱篷变作岩漰,这应该也只是白族话翻译成汉字后常见的变化。根本不可能是1962年刻成的碑里说的那样。“漰”字的意思是岩边水潭。岩棚旧有的一个岩边大水潭却在岩棚山东头村外山根脚的一堵大石岩下,是一个不很大的水潭,在龙津桥北面十几米处。每每月亮从龙津桥东面的垭口冒出来,影子落在那个小谭里,水潭太小,月影就显得特别的大,所以岩棚老年协会的一面白墙上还大大的写了“漰泉映月”四个充满无限美景的大字。许多人说这就泉水是岩棚村原来村名岩湔的来历,可是这个水潭离本主庙却最少得有一公里,水潭在最东边,本主庙却在村子靠西边的山下,并且在《雍正宾川州志》里,岩棚村名是翻译作崖棚,说是因为粱本主的事,而把莱篷改作岩漰,估计是后人在讲述这个故事时的附会穿凿吧。
这岩下水潭附近的荒草从中有一个土堆,排营坝子的人们都知道那是万人冢。那是咸丰年间,大理回民杜文秀带领大理各族人民奋起反抗满清朝廷的腐朽统治,遥尊太平天国天王为主,被天王封为总领兵马大元帅,在大理建立了以大元帅府为中心的地方政权,与清庭抗争了十八年。期间因为宾川宾居的回民响应起义,攻破了牛井太和大营,清政府为了阻止两股军队会师,紧急抽调白族名将杨玉科率兵开进大理,在岩棚村东面咽喉要道龙津桥附近扎营,卡住了宾川与大理之间联通的道路。于是回民义军与满清军勇在排营坝子一带拉锯一般争夺了好多年,双方都伤亡很大。在某一年的大年初一,义军趁着清军过大年,发动了对龙津桥驻军的突袭,把清军杀得片甲不留,悲催的是,很多岩棚乡邻也被波及,据说有人被害后,断了的脖颈处还滚出了刚吃下去的元宵,那血一直流到了文昌宫门口。老人家一说起这件被称为“红(清军)白(义军)旗事件”的悲惨往事时,都会痛心疾首,凄凉的说到:那血啊,一直流到了寺(文昌宫被当地人叫着大寺)背后……后来人们收拾那个时期所有暴尸荒野的凄凄白骨,一起葬在龙津桥附近的一个大坑里,修成了一个巨冢,那就是现在所说的万人冢,排营坝子唯一的武举人袁绍魁曾经在那儿题了一块碑,记述这件悲惨的往事……

那被称为“寺”的文昌宫后来发展成了岩棚小学,文昌帝君则被恭请到了本主庙一起祭拜。只是可惜因为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现在那建设完善的岩棚小学也已经被闲置,学生都被并到了排营完小,只是苦了现在这些孩子和家长了。同文昌宫一样,也座落在本主庙里的观音阁,据说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只是古迹被毁,现在这个阁楼也是二十多年前由岩棚莲池会自发重建的。
经历许多浩劫,原来那些常来祭拜万人冢的外乡人早没了后续,不过万人冢的一块副碑在最近居然被发现了,散落在荒草丛中,依然完好无缺,上面那武举人题的碑铭都还清晰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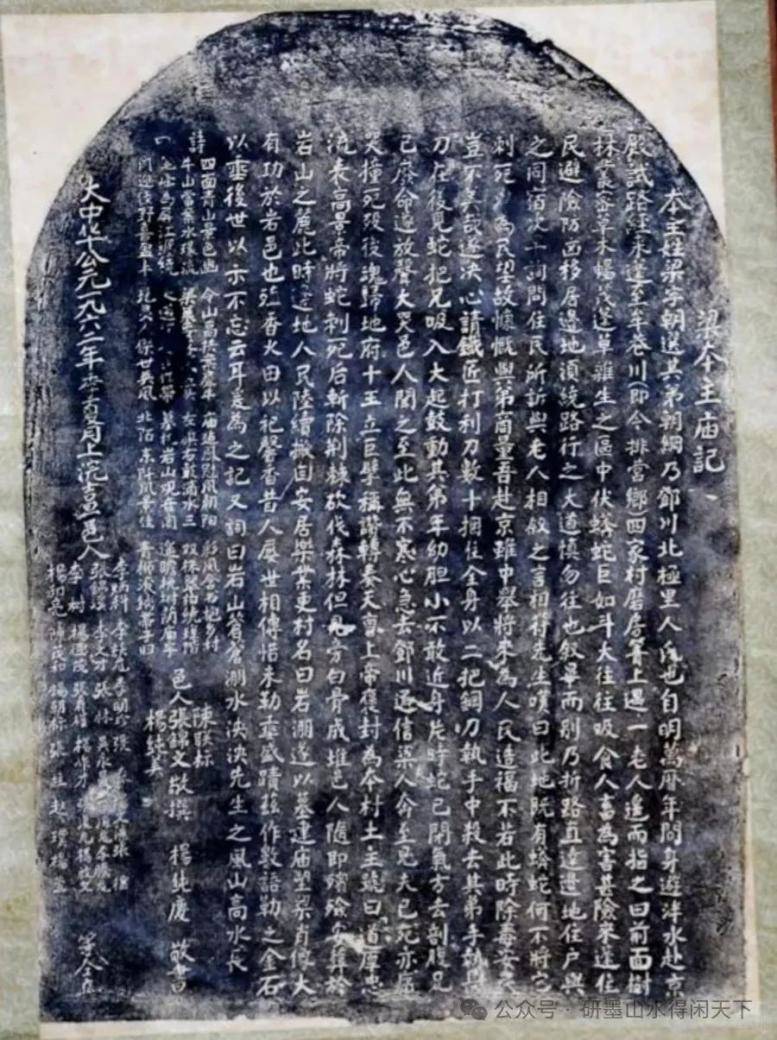
岩棚村满清末期曾出现一个杨大老爷,都说这杨大老爷有十几个大小姨太太,只是因为没机会去走访,不大知道这杨大老爷的辉煌往事,只知道他最小的重孙都与我差不了几岁。
岩棚现在是排营坝子主要的葱蒜交易市场,在蒜苔蒜头上市的时候,附近萂村坝子、瓦溪坝子,甚至大营坝子都有人把作物拉倒岩棚去交易。
作为排营坝子的第二大村,排营坝子的行政中心、教育中心都曾经被短暂的搬迁到岩棚过,解放初期的排营粮点就设在岩棚。在我们上小学五六年级时,我们杨老师比较喜欢的几个同学,还一起去岩棚的粮点帮杨老师领过国家供应的大米。粮点院里有一棵巨大的桑树,漆黑的桑椹很甜,一直记得一起去给我们杨老师领粮时,我那幼小心灵里的女神,吃我给她采摘的桑椹,丹唇都吃成了炫酷的乌黑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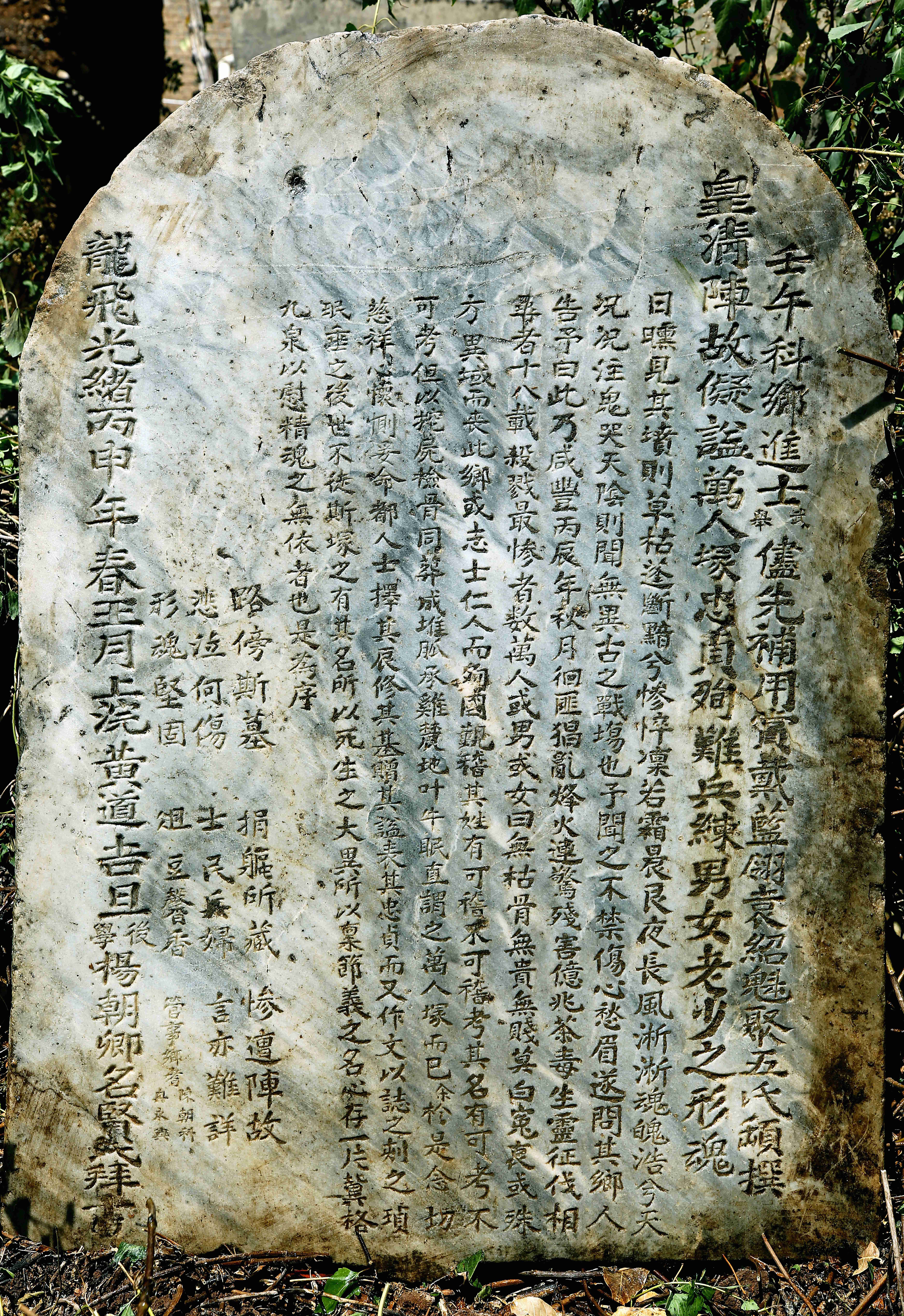
附:岩漰万人冢碑文
壬午科乡进士(左皋右氏)武举(左武右举)尽补用赏戴蓝翎袁绍魁聚五氏顿撰。皇清阵故疑谥万人冢忠贞殉难兵练男女老少之形魂。日曛见其坟,则草枯蓬断,黯兮惨悴,凛若霜晨,艮夜长风淅淅,魂魄浩兮天,况况注鬼哭,天阴则闻,无异古之战场也,予闻之,不尽伤心愁眉,遂问其乡人,告予曰:此乃咸丰丙辰年秋月,回匪猖乱,烽火连惊,残害亿兆,荼毒生灵,征伐相寻者,十八载杀戮,最惨者数万人,或男或女,曰无枯骨,无贵无贱,莫白冤哀,或殊方异域,而丧此乡,或志士仁人,而殉国觐,稽其姓,有可稽不可稽,考其名,有可考不可考,但以挖尸捡骨,同葬成堆,脉承鸡麓,地叶牛眠,直谓之万人冢而已余,于是念及慈祥,心怀恻馁,命都人士,择其辰,修其墓,赠其谥,表其忠贞,而又作文已志之,刻之玧珉,垂之后世,不徒斯冢,之有其名,所以死生之大异,所以禀节义之名,心存一片,冀格九泉,以慰精魂之无依者也,是为序:
路傍斯墓,捐躯所藏,惨遭阵故,悲泣何伤;
士民兵妇,言亦难详,形魂坚固!俎豆馨香。
管事乡者:陈朝科,冉永兴龙飞光绪丙申年春王月上浣吉旦
后学杨朝卿名贤弋拜书
作者/(申研墨)杨志勇
编辑/杨宏毅
责编/杨宏毅
审稿/张进
终审/杨凤云
投稿邮箱/bcrmtzx@163.com


网友评论文明上网,理性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