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川时讯•文化周刊】我的奶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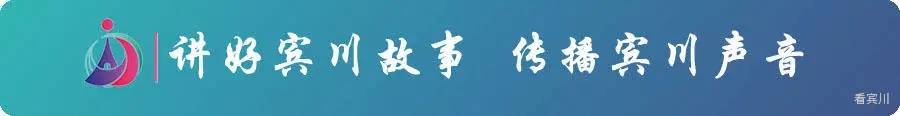


◎/乔献花
奶奶今年87岁了,头发白得像落了层雪,她的眼睛笑起来会弯成月牙,眼角的皱纹像被阳光晒软的棉线,层层叠叠都是温柔。奶奶的坚强,是藏在岁月里的韧劲。奶奶是闲不住的。她最爱做和经常做的两件事是做手工香和手工背绳,奶奶做的手工香很好烧,村里和附近的村子都喜欢和奶奶买,奶奶做的手工背绳也很受欢迎。
奶奶的慈祥,是融化在日常里的糖;那些藏在皱纹里的故事,早已成了我心里最亮的光。
在我很小的时候,印象中的奶奶戴着头巾在楼上做香,每次下来都灰突突的。有时候我好奇,也会上去看奶奶做香。奶奶做香的原材料都是她在山上找的,香叶,还有一种会粘的树根,还有艾草的枝条。香叶晒干打成粉,分成粗面、细面两种。会粘的那种树根打碎搅在水桶里,艾草的枝条修成长短、粗细相等的段。奶奶首先拿着一把艾草的枝条,放在会粘的桶里泡一下水拿出来,然后在铺开的粗香面上,上下来回拍打。翻来翻去的泡水、拍打好几次,香面粘得比较均匀了之后把香排成一排一排的晾干。过两天香干得差不多了奶奶又把所有的香再泡一次粘水,然后再裹一层更细的香面,然后又一支一支的倒立在墙边晾干。奶奶做香的画面时常在我脑海里浮现。奶奶的那些原材料我都和奶奶一起去找过,去山上砍香叶,晾晒。去田埂上挖那个会粘的树根,那个树根我至今都记得长什么样也知道哪些地方能挖到,但是叫不出名字。还和奶奶一起去找艾草的枝条,那种长得比较直、比筷子稍微粗一点的枝条是我们最喜欢的,用镰刀割下来之后一个枝条可以砍出来三小段,然后捆成一捆。
 奶奶做香做了几十年了,一到清明节,七月半,过年。奶奶会提前做好很多的香背到镇里的集市上卖,附近的村民也会到家里来买。奶奶前几年都是在三叔家住,三叔家的两层木制小楼,楼上就是奶奶的制香场地。后来的几年,奶奶去县城给小姑带孩子,做香就没有那么方便了,那个时候的奶奶快70岁了,身子骨还算硬朗,奶奶隔三差五的也会回三叔家做香,然后带下去县城里卖,奶奶还学着县城里其他卖香的人的样子,在香上面裹上一层红色的软纸,过年过节的时候烧,比较喜庆。价格也比普通的香卖得好一些。后来的几年,奶奶不能经常上山下地的找原材料了,就没有做香了,奶奶又开始做背绳了。
奶奶做香做了几十年了,一到清明节,七月半,过年。奶奶会提前做好很多的香背到镇里的集市上卖,附近的村民也会到家里来买。奶奶前几年都是在三叔家住,三叔家的两层木制小楼,楼上就是奶奶的制香场地。后来的几年,奶奶去县城给小姑带孩子,做香就没有那么方便了,那个时候的奶奶快70岁了,身子骨还算硬朗,奶奶隔三差五的也会回三叔家做香,然后带下去县城里卖,奶奶还学着县城里其他卖香的人的样子,在香上面裹上一层红色的软纸,过年过节的时候烧,比较喜庆。价格也比普通的香卖得好一些。后来的几年,奶奶不能经常上山下地的找原材料了,就没有做香了,奶奶又开始做背绳了。
 奶奶做背绳也是从原材料开始就自己准备,她经常找来一些各种颜色的口袋,一根一根的线被抽出来,左一捆右一捆的放着。遇到颜色独特一点的口袋奶奶就会很开心,因为那样拆出来的线会好看一些,做出来的背绳也会很独特。有时候我去看奶奶,经常看见她裤脚拉起来一只,在认真的搓着背绳。她告诉我牛井县城里买这个背绳的少,有时候做了也卖不出去,还是要回我们镇上卖。村里的人们打核桃,背草,做各种农活都用得。所以80多岁的奶奶还是会经常去镇上的集市卖她做的背绳。现在奶奶又回来和三叔家住了,奶奶说回三叔家之后卖背绳都方便多了。三叔说:“你奶奶天天都问,哪天是星期一啊,我要去镇上卖背绳了”。我们会给奶奶钱,给奶奶买吃的、穿的。也劝她别做那些了,经常做伤眼睛,腰也不好,但是奶奶就是不听,依然坚持做着,我们也就随她了。也许一直有事做,奶奶才那么精神吧!
奶奶做背绳也是从原材料开始就自己准备,她经常找来一些各种颜色的口袋,一根一根的线被抽出来,左一捆右一捆的放着。遇到颜色独特一点的口袋奶奶就会很开心,因为那样拆出来的线会好看一些,做出来的背绳也会很独特。有时候我去看奶奶,经常看见她裤脚拉起来一只,在认真的搓着背绳。她告诉我牛井县城里买这个背绳的少,有时候做了也卖不出去,还是要回我们镇上卖。村里的人们打核桃,背草,做各种农活都用得。所以80多岁的奶奶还是会经常去镇上的集市卖她做的背绳。现在奶奶又回来和三叔家住了,奶奶说回三叔家之后卖背绳都方便多了。三叔说:“你奶奶天天都问,哪天是星期一啊,我要去镇上卖背绳了”。我们会给奶奶钱,给奶奶买吃的、穿的。也劝她别做那些了,经常做伤眼睛,腰也不好,但是奶奶就是不听,依然坚持做着,我们也就随她了。也许一直有事做,奶奶才那么精神吧!
当然,奶奶也不是一直那么坚强的。我妹妹在昆明工作,她每次回来,大家都回老家聚一下,她会带很多好吃的回来,然后我们叫奶奶过来家里吃饭。奶奶看着一桌子好吃的,又和我们讲起以前的事情,讲着讲着就哭了,奶奶说:“以前的我们多难啊,孩子多,吃的也没有,孩子没奶喝,给我急了作哭啊”!话匣子一打开,奶奶的话就忍不住,泪水也忍不住。我们姐妹俩不知道该怎么劝,眼泪在眼睛里打转的陪着奶奶。奶奶的泪,从不是软弱的痕迹。那些泪里,藏着对孩子的疼惜,藏着熬过苦难的心酸。
 她总说现在的日子太好,好到让她想起过去就忍不住流泪。可我知道,那些落进旧时光里的泪,早已浇灌出了今日的安稳,也成了我们心里最该珍惜的念想。
她总说现在的日子太好,好到让她想起过去就忍不住流泪。可我知道,那些落进旧时光里的泪,早已浇灌出了今日的安稳,也成了我们心里最该珍惜的念想。
作者/乔献花
编辑/杨宏毅
责编/杨宏毅
审稿/张 进
终审/杨凤云
投稿邮箱/bcrmtzx@163.com


网友评论文明上网,理性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