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摄宾川】诗意南坡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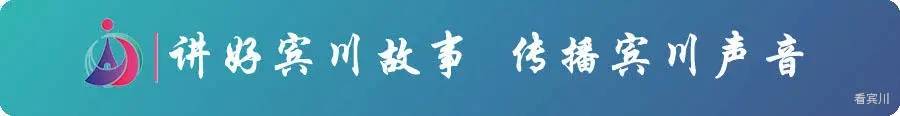


◎ /杨树荣
宾川县的南坡村,这个被鸡足山温柔拥在南麓山坡上的村落,没有喧嚣古镇的拥挤,也无网红村寨的浮躁,只以“房在树林中,人在风景里”的模样,把日子过成了诗。
南坡村70多户、270多人,大多姓乔。离村不远的一方斑驳的墓碑,静静记载着村落的源头祖先乔选。关于这份乔姓的渊源,还藏着一段与明朝年间相关的传说。据说当年有位皇帝有个妹妹,生就一副喜静厌闹的性子,看惯了宫中的雕梁画栋、尔虞我诈,反倒对山野间的晨钟暮鼓心生向往,执意要带发修行。皇亲国戚们苦劝无果,最后只得备下轿子,派了乔、敫、毕、字四姓之人,一路护送她到鸡足山大觉寺。皇姑住山修行后,念及四姓之人一路辛劳,又远离故土,便将四人分别安顿在山下这片向阳的地方,乔姓便成了南坡村最初的先民。几百年过去,皇姑早已圆寂,安葬在大觉寺后山峰的树林间,那方小小的墓冢,伴着山间的清风与晨雾,默默守护着山下这方她曾牵挂的烟火人间。
 岁月的车轮滚滚向前,南坡村也在风雨中历经了几番沧桑。村中一位80多岁的老人讲,20世纪初,村里的房屋还多是低矮的茅草房,屋顶铺着晒干的茅草,墙壁是黄泥夯实的,一到雨季便漏雨,寒冬时冷风又从墙缝里钻进来,日子过得清苦。民国年间,匪患猖獗,一群土匪突然闯入村落,一把大火烧尽了所有茅草房,浓烟滚滚中,村民们只能扶老携幼逃进山林,待土匪离去,只余下一片焦黑的断壁残垣。直到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南坡村才迎来了新生。村民们带着对家园的期盼,一砖一瓦、一木一梁地重建房屋,泥土混合着汗水,在山坡上重新筑起了家。1953年,乔家大户牵头建起了一栋三层木楼,原木的纹理透着温润,飞檐翘角带着白族建筑的精巧,在当时的沙址坝及四邻八乡中格外惹眼,每当有人路过,总要驻足仰望,赞叹这栋木楼的气派。
岁月的车轮滚滚向前,南坡村也在风雨中历经了几番沧桑。村中一位80多岁的老人讲,20世纪初,村里的房屋还多是低矮的茅草房,屋顶铺着晒干的茅草,墙壁是黄泥夯实的,一到雨季便漏雨,寒冬时冷风又从墙缝里钻进来,日子过得清苦。民国年间,匪患猖獗,一群土匪突然闯入村落,一把大火烧尽了所有茅草房,浓烟滚滚中,村民们只能扶老携幼逃进山林,待土匪离去,只余下一片焦黑的断壁残垣。直到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南坡村才迎来了新生。村民们带着对家园的期盼,一砖一瓦、一木一梁地重建房屋,泥土混合着汗水,在山坡上重新筑起了家。1953年,乔家大户牵头建起了一栋三层木楼,原木的纹理透着温润,飞檐翘角带着白族建筑的精巧,在当时的沙址坝及四邻八乡中格外惹眼,每当有人路过,总要驻足仰望,赞叹这栋木楼的气派。
 如今走近南坡村,早已不见当年的茅草房与焦土,取而代之的是错落散居的民房,白墙黛瓦映着绿树,连空气里都飘着草木与果香。漫山遍野的杨梅树是村里的好风景,春末夏初之时,枝头缀满了鲜红的杨梅,果香漫过村落和山野。深秋时节,村里古老的核桃树枝干粗壮,枝桠向四周舒展,像一位位年迈却健壮的老者,守护着村落,树下偶尔能捡到几颗掉落的核桃,剥开外壳,果肉饱满香脆,满是自然的清甜。
如今走近南坡村,早已不见当年的茅草房与焦土,取而代之的是错落散居的民房,白墙黛瓦映着绿树,连空气里都飘着草木与果香。漫山遍野的杨梅树是村里的好风景,春末夏初之时,枝头缀满了鲜红的杨梅,果香漫过村落和山野。深秋时节,村里古老的核桃树枝干粗壮,枝桠向四周舒展,像一位位年迈却健壮的老者,守护着村落,树下偶尔能捡到几颗掉落的核桃,剥开外壳,果肉饱满香脆,满是自然的清甜。
 除了杨梅与核桃,南坡村还有板栗、木瓜、苹果。每到雨季,山林间还会有野生菌,鸡枞、松茸、牛肝菌。村里还种植有附子、重楼、黄精、石斛等药材,成为南坡村名副其实的宝藏。
除了杨梅与核桃,南坡村还有板栗、木瓜、苹果。每到雨季,山林间还会有野生菌,鸡枞、松茸、牛肝菌。村里还种植有附子、重楼、黄精、石斛等药材,成为南坡村名副其实的宝藏。
 站在村里稍高一点位置的任何一个角落,往北望去,都能清晰看见鸡足山的天柱峰,山峰直插云霄,山间云雾缭绕,更显巍峨。天气晴朗之时,最惹眼的莫过于金顶楞严塔,塔身在阳光下泛着淡淡的金光,哪怕隔着一段距离,也能看清塔的轮廓,仿佛一位沉默的守望者,静静矗立在山巅,与南坡村遥遥相望。此时若是闭上眼,仿佛能听见山间的钟鼓声,顺着风飘下来,落在耳边,让人瞬间静下心来,所有的烦躁与疲惫都烟消云散,只剩“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的惬意。
站在村里稍高一点位置的任何一个角落,往北望去,都能清晰看见鸡足山的天柱峰,山峰直插云霄,山间云雾缭绕,更显巍峨。天气晴朗之时,最惹眼的莫过于金顶楞严塔,塔身在阳光下泛着淡淡的金光,哪怕隔着一段距离,也能看清塔的轮廓,仿佛一位沉默的守望者,静静矗立在山巅,与南坡村遥遥相望。此时若是闭上眼,仿佛能听见山间的钟鼓声,顺着风飘下来,落在耳边,让人瞬间静下心来,所有的烦躁与疲惫都烟消云散,只剩“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的惬意。
 南坡村春夏秋冬好景致,若是到村里走亲访友,也许会让人想起孟浩然笔下的《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的美好诗句,诗的意境与现实的情景美妙结合,令人心旷神怡,许久不想离开。
南坡村春夏秋冬好景致,若是到村里走亲访友,也许会让人想起孟浩然笔下的《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的美好诗句,诗的意境与现实的情景美妙结合,令人心旷神怡,许久不想离开。
 现在,南坡村的村民们不仅靠种植果树、药材过日子,还依托鸡足山的旅游资源,上山开展旅游服务业,开始在家创办农家乐。白族风格的院落里,摆上干净的桌椅,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吃农家菜、住民宿,白天去山间赏景、采摘,傍晚坐在院子里看夕阳染红鸡足山的山峰,听虫鸣鸟叫,感受远离城市喧嚣的宁静。这里没有刻意打造的网红打卡点,只有最原生态的风景和最淳朴的人情。南坡村将成为观风赏景、驻足休闲、采风考察、寻找诗意最好的地方。
现在,南坡村的村民们不仅靠种植果树、药材过日子,还依托鸡足山的旅游资源,上山开展旅游服务业,开始在家创办农家乐。白族风格的院落里,摆上干净的桌椅,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吃农家菜、住民宿,白天去山间赏景、采摘,傍晚坐在院子里看夕阳染红鸡足山的山峰,听虫鸣鸟叫,感受远离城市喧嚣的宁静。这里没有刻意打造的网红打卡点,只有最原生态的风景和最淳朴的人情。南坡村将成为观风赏景、驻足休闲、采风考察、寻找诗意最好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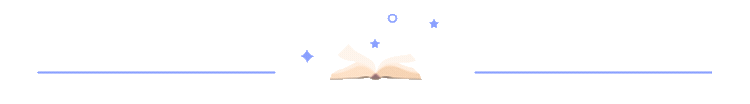
作者/杨树荣
编辑/杨宏毅
责编/李丹
审稿/朱晓天
终审/杨凤云 张进



网友评论文明上网,理性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