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川时讯·文化周刊】葡萄藤下的星光



◎/李红文
这几天,地里没活儿。葡萄藤正歇着,积蓄着下一轮甜。她却歇不住。清晨,天还青灰着,她便和同村的几个伴当,骑着车往邻村的大豆地去了。临出门,戴着头盔手套,骑上电瓶车,回过头对我说:“地里闲着也是闲着,我去摘豆子。我们不能全家靠你一个人养活,我也要去苦点钱。” 声音不高,像晨雾一样轻,却沉甸甸地落在我心上。门帘一掀,她的人影便融进那灰扑扑的曙色里了。
我立在院子里。这院子,白日里是她的天下。此刻却空落落的。角落里堆着些农具,铁锹的木把被她的手磨得光滑。空气里有股子清冽的、混合着泥土与葡萄叶子的气味。再过些时辰,日头毒起来,这气味便会发酵成一种稠厚的、阳光晒透植物的暖香。我忽然觉得,这院子,这家,像一口钟,平日里因着她的忙碌叮当作响,此刻她一走,便静得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回声。这静,让人心里发慌。
 今天是周末,难得有时间去看看葡萄地。
今天是周末,难得有时间去看看葡萄地。
我们家的葡萄地,就在村口处的山上,家里可直接看见山上安装的太阳能灯,十多亩,连成一片。当初决定种葡萄,是她拿的主意。她说,光靠你那点死工资,心里不踏实。孩子要上学,老人要看病,日子得像藤蔓一样,自己会抓着地皮往前爬才行。于是,我们便有了这片葡萄地。春来抹芽,夏日疏果,秋季采摘,冬日埋土,哪一样不是功夫?哪一样不是汗水?这些活儿,多半压在她肩上。我只能在周末,像个生疏的帮手,在她指点下,做些边角的活计。她的手,早已不是当年恋爱时的模样了,关节粗了些,掌心有一层薄而硬的茧,指甲缝里,总也洗不尽泥土的淡褐色。
我走进地里。晨露还没散尽,凉津津地打在裤脚上。藤蔓一架一架的,葡萄叶虽已干枯却整齐地排开,像是大地沉默的琴弦。阳光透过干枯的叶子筛下来,光斑在土地上轻轻晃动。
 她套种的莴笋已经绿油油的一片了……
她套种的莴笋已经绿油油的一片了……
这一刻,我仿佛看见她了。不是此刻在豆子地里弯腰的她,而是无数个清晨与黄昏,在这葡萄架下的她。我看见她扛着沉甸甸的化肥袋子,咬着牙,一步一步走得踏实;看见她仰着头,举着剪子,在错综的藤蔓间寻找该疏去的果穗,侧脸被阳光镀上一层金边,神情专注得像在完成一件圣洁的功课;看见雨前,她急匆匆地盖防雨布,风把她的头发吹得凌乱;看见卖完一季葡萄,她坐在炕沿上,蘸着唾沫,一张一张仔细数那些皱巴巴的票子,眉头微微蹙着,算计着哪一笔该存,哪一笔该还,哪一笔能给女儿添件新衣裳……这片绿海里的每一片叶子,每一颗果实,都浸透了她的汗,她的盼,她的沉默的力气。
 “我也要去苦点钱。” 这话,哪里只是一句关于摘豆子的言语?这分明是这些年,她在这片葡萄地里,早已践行了千百遍的生命宣言。她用她的方式,倔强地、一刻不停地,与我共同扛着这个家。我那份从学校带回的工资,是看得见的保障;而她从土地里刨挖出的、从指尖节省下的,是更深沉、更绵长的底气。我们不曾说过什么“同心”的漂亮话,可这日子,这土地,早把我们俩的根须,紧紧缠在一起了。
“我也要去苦点钱。” 这话,哪里只是一句关于摘豆子的言语?这分明是这些年,她在这片葡萄地里,早已践行了千百遍的生命宣言。她用她的方式,倔强地、一刻不停地,与我共同扛着这个家。我那份从学校带回的工资,是看得见的保障;而她从土地里刨挖出的、从指尖节省下的,是更深沉、更绵长的底气。我们不曾说过什么“同心”的漂亮话,可这日子,这土地,早把我们俩的根须,紧紧缠在一起了。
傍晚,西边的天上烧起了霞,葡萄叶子都染上了一层暖暖的、橙红的光晕,像醉了一样。
 天基本黑了,她回来了。头发有些蓬乱地贴着额角,脸上带着日晒后的红晕,眼睛里有着明显的倦色,但看见我,那倦意里便漾开一点极淡的笑意,像石子投入静湖,漾起的第一圈涟漪。
天基本黑了,她回来了。头发有些蓬乱地贴着额角,脸上带着日晒后的红晕,眼睛里有着明显的倦色,但看见我,那倦意里便漾开一点极淡的笑意,像石子投入静湖,漾起的第一圈涟漪。
“回来啦?”我说。
“嗯。”她拍拍身上的尘土,“豆秸子扎人得很。”“今天一起去的,我摘大豆又得了第一名。”
我们一前一后进了屋。桌上饭菜已摆好。她没有说什么,只是洗了手,坐下,端起碗,喝了一大口菜汤。然后,很轻地,舒了一口气。那口气里,有劳累,也有一种到家的安然。
窗外,天完全黑了。明天,她或许还要去摘豆子,或许葡萄地又有新的活计。日子,就是这样周而复始。
 但我知道,我们就像那葡萄藤。两根藤,各自迎着风雨,伸向天空,努力去触摸阳光与雨露。可在地底下,我们的根,却紧紧相连,在看不见的黑暗里,相互输送着养分,分担着重压,也分享着一点点湿润的慰藉。这联结,沉默无言,却比任何言语都牢固;这联结,让每一颗最终酿出的果实,都带着两份阳光的味道,两份生命的甜。
但我知道,我们就像那葡萄藤。两根藤,各自迎着风雨,伸向天空,努力去触摸阳光与雨露。可在地底下,我们的根,却紧紧相连,在看不见的黑暗里,相互输送着养分,分担着重压,也分享着一点点湿润的慰藉。这联结,沉默无言,却比任何言语都牢固;这联结,让每一颗最终酿出的果实,都带着两份阳光的味道,两份生命的甜。
夜空中,星星出来了,一颗,两颗,清亮亮地,缀在屋角的上方,静静地照着这人间的、相依为命的温暖。
图文/李红文
编辑/杨宏毅
责编/杨宏毅
审稿/张 进
终审/杨凤云
投稿邮箱/bcrmtzx@163.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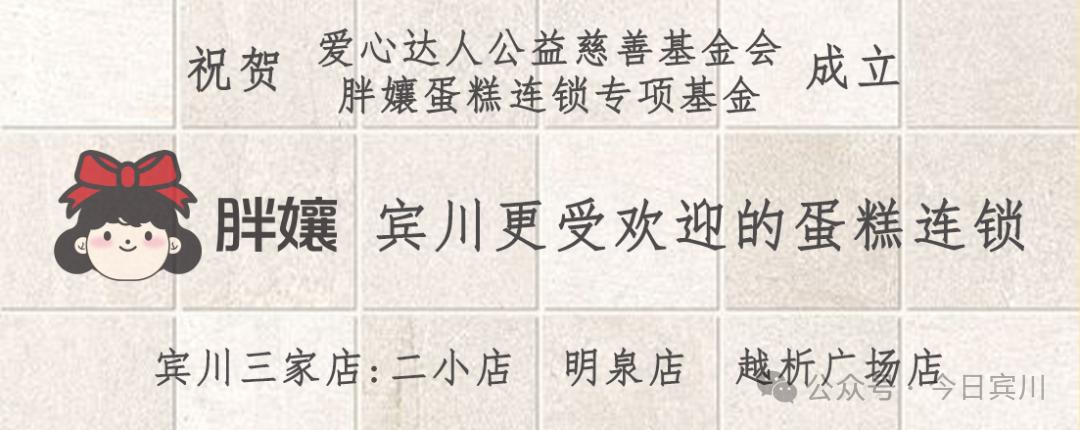



网友评论文明上网,理性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