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川时讯·文化周刊】拉乌山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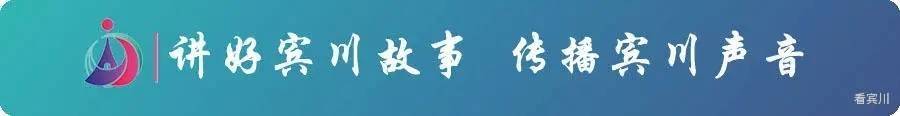


◎张若恒
有一个人,靠一片核桃,种一块地,养一群牛,领一条狗,喝一杯烧酒,抽一袋旱烟,住着一幢木屋慢慢老去。
有一幢木屋,看着一片土地,陪着一个人,守着一群牛,依偎着一条狗,燃着一塘火,也在慢慢老去。
拉乌是核桃之乡,山坳里山岭上有大片大片的核桃林,核桃林中有一座座木头建的房子,记忆里阿公阿婆就住在这小小的木头房子里。拉乌是典型的山区乡镇,水田少旱地多。水田在低海拔的河谷两岸,旱地在高海拔地区。

山区人家每家每户都有一片核桃园,核桃林边都有几块自己家的耕地。核桃林和耕地离村庄都比较远,步行大多都要走一两个小时,为了有更多的劳动时间,许多村民在核桃林边建起了垛木房。把房子建成垛木房,是因为取材方便,建造简单。在核桃林中选一块平整、背风向阳的空地,把地整平,计划建多大的房子,就在长方形或是方形地面的四角放上一块平整的大石头,基础就算完工。下一步是到森林中选取粗细合适的栗木,木头的长度根据房子的大小而定。栗木是建垛木房的最好材料,用冬季砍的栗木建的垛木房,要是不淋雨四五十年都不会朽。选取木料的地方不远,一般不会超过一公里。供两个人住的一幢垛木房,两个男人五天之内可以建好。大多都是建一楼一底的两幢,一幢住人,一幢关牲口。
 阿公家在离村庄六公里的地方有一片核桃树和八九亩地,林中有两幢小垛木房,以前只是在收种时节住在那里,儿子成家后,家里的大事小事都用不着阿公阿婆操心,阿公阿婆就一年四季住在核桃林边的垛木房中。垛木房一边有一个火塘,这是做饭取暖的地方,另一边就是床。
阿公家在离村庄六公里的地方有一片核桃树和八九亩地,林中有两幢小垛木房,以前只是在收种时节住在那里,儿子成家后,家里的大事小事都用不着阿公阿婆操心,阿公阿婆就一年四季住在核桃林边的垛木房中。垛木房一边有一个火塘,这是做饭取暖的地方,另一边就是床。
早上起来,阿婆在院子里撒上一碗玉米,几十只鸡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哄而上争着啄食玉米,不到一分钟地上的玉米一扫而空。有的鸡知趣的离开,有的鸡还在院子里转悠,东瞅瞅西瞅瞅希望再能发现一两粒玉米。阿婆拿起棍子在地上使劲的敲打几下,最后的几只鸡只能很不情愿的离开,很快所有的鸡都消失在树林里。他们用爪子掀翻树叶刨开泥土,寻找下面的虫子,实在是找不到足够的虫子时嫩草也啄食。太阳落山,林子里的鸡回到垛木房周围转,东看西看,看到阿婆它们就很兴奋,阿婆走到哪里它们就跟到哪里,阿婆照例是舀一碗玉米撒在地上,鸡疯狂的争食。吃过玉米,大鸡陆陆续续飞上核桃树,晚上它们就在核桃树上过夜,小鸡仔跟着妈妈回到鸡窝,钻进妈妈腹下暖暖的睡觉。
天刚蒙蒙亮,阿公起来燃起火塘烤茶。阿公先把茶罐烧烫,再把茶叶放到茶罐中,阿公抖动茶罐,茶叶在茶罐中上下翻滚,等能够闻到茶香时,阿公把烧得沸腾的开水注入茶罐,嗤的一声,茶水在罐里翻滚。“碎米他妈来吃茶。”阿公喊。阿婆放下手中的锄头从菜园回到房中,坐在火塘边。边喝茶阿婆边对阿公说:“茶吃了你去挖地,这几天核桃叶掉光了赶紧挖翻一下,把核桃叶挖翻在地里,不让风吹走。”整个冬季的早晨阿公就是挖地,挖完核桃树下的地再挖玉米地。阿公挖地时,鸡总是跟在后面寻找从土里翻出来的虫子,公鸡发现虫子赶快向母鸡献殷勤,母鸡发现虫子急着呼唤孩子。
吃完茶阿婆把罗锅里的米淘洗好,把罗锅放到三脚上,在火塘里添上适当的柴就向山坡上的松林走去。松林下落满了金黄色厚厚的松针,阿婆用耙子把松针摞到一起,用两根绳子捆起来背到牛圈周围堆起。一个冬季阿婆把几个山岭的松针都背了回来,看着一堆堆像小山一样的松针,阿婆心里美滋滋的,心想来年牛羊睡在软软的松针上一定很舒服,牛粪、羊粪与松针一起踏出来的粪背到玉米地里,玉米棒子一定又长又饱满,背到核桃树下,核桃一定又大又肥。背够了松针阿婆又背柴,在冬季要把一年烧的大部分柴储备好,柴垛在院子边上差不多和阿婆一样高,平时阿公放牛看到干柴也会时不时扛回来几根。
 春去秋来季节变换,春种秋收阿公阿婆总是干不完手中的农活,不过也好,阿公阿婆只要是闲上一天就浑身不自在,干着农活心里才踏实。
春去秋来季节变换,春种秋收阿公阿婆总是干不完手中的农活,不过也好,阿公阿婆只要是闲上一天就浑身不自在,干着农活心里才踏实。
阿婆认为女人做饭、喂猪、喂鸡、洗衣服是天经地义,所以这些事阿公是从来不用管的。不过每日两餐都很简单,好在阿公不挑食没有对饭菜提过半点意见。每顿饭,菜不超过两样,菜的种类随季节变换,菜园里有什么,楼上有什么,山上能采到什么就吃什么,更多的时候应该是阿婆想起吃什么就吃什么。冬季篱笆围成的菜园里是白胖的萝卜、肥嫩的青菜,夏季地埂上睡满了水嫩的南瓜、架上结满饱满的四季豆。当然无边的山野也在随季节提供美味的菜肴,春天的山芹菜、香菇、树头菜,夏天的菌子都是要成为阿公阿婆的菜肴。猪肉挂在火塘上方,洋芋、南瓜堆在楼上,没有挖完的洋芋还埋在土里。“聪明”的母鸡总想把蛋藏起来,但绝大多数都会被阿婆发现,两三天阿婆就收一次鸡蛋,每次只要留一个鸡蛋在鸡窝里,母鸡看到有蛋在窝里心情很好,每次下蛋前都要高声的向同伴和阿婆炫耀一番。有母鸡产的蛋没有被阿婆发现,等阿婆看到时蛋已经变成了小鸡仔,小鸡跟在妈妈身后欢快的唱着歌。
吃过早饭阿公打开圈门,五头牛和十二只羊挤出圈门朝盐巴槽冲去,在羊出来之前阿公已经在槽里撒上了盐巴,此时牛羊正在贪婪的舔食盐巴,直到再也舔不出盐味才很不情愿的离开。牛羊的盐巴槽是用一根大碗口粗的水冬瓜树砍凿出来,一根三米左右的圆木,顺着木头在上面凿一条差不多和木头一样长的小槽就成。阿公带上所有装备跟着牛羊朝深山走去,阿公每天的装备都一样,穿一件羊皮卦,挎一个挎包,挎包里放一把柴刀、一袋旱烟、一只烟锅、一块塑料布。
放牧的森林牛羊不知道有多大,反正它们从来没有走到过尽头,它们会穿过丛林,走过草甸,翻越山岭。除了自己之外阿公很少见到另一个人,他只能如大山一般沉默,打破寂静的是清脆的鸟叫,是吹过森林的风,是母羊咩咩的呼唤,抬起头一朵云撞进阿公的心里,林中悄然开放的杜鹃,每年都会关顾阿公慢慢灰暗的瞳孔。虽然没有人和阿公说话,但他早已经习惯了不与人说话,而是内心与身边的事物交流。
 包产到户后村里的生活渐渐好了起来,很多有能力的家庭都想盖大瓦房,进入冬季,村里的各家各户能批到一点砍伐木材的指标,村里的男人赶着骡子驮着铺盖、炊具进山伐木,在山里一住就是两个月。现在村里开始建小洋楼,以前建房的木头都渐渐在火塘里变成了灰。看到自己砍倒大树后留下的树桩,阿公心里不是滋味,这么大的树要长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在这林中,自己有生之年是再也见不到这么大的树了。
包产到户后村里的生活渐渐好了起来,很多有能力的家庭都想盖大瓦房,进入冬季,村里的各家各户能批到一点砍伐木材的指标,村里的男人赶着骡子驮着铺盖、炊具进山伐木,在山里一住就是两个月。现在村里开始建小洋楼,以前建房的木头都渐渐在火塘里变成了灰。看到自己砍倒大树后留下的树桩,阿公心里不是滋味,这么大的树要长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在这林中,自己有生之年是再也见不到这么大的树了。
放牲口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但阿公每天都很忙,没有闲着就不会空虚。树洞里的蜜蜂做了多少蜜阿公常常要去看,季节到了野天麻有没有发芽阿公要去瞧瞧,春天的水芹菜、香椿、香菌等着要采,夏季、秋季林中的菌子突突往上冒,一天不采就烂掉,阿公整天忙在森林中,操心在森林上,放牧反而成了他的副业。
没有要紧的事要办或者走累了,或者什么都懒得想时,阿公随手摘一片叶子含在两唇间,悠扬的曲调在旷野中飞扬,随着飘飞的是阿公的思绪。阿公的思绪回到了刚认识阿婆时,那时阿公十八岁,阿婆十六岁,是这优美的声音让他们相识、相恋到成家。曾经的心跳归于平静,过去的憧憬已经消磨。五个儿女都长大成人,四个成家立业,最让阿公放心不下的是老幺姑娘,读了大学但不安于平淡,爱折腾,满世界的跑。
山高林深湿气重,阿公每顿饭前都饮酒,中午一杯,晚上两杯。吃饭之前阿婆把酒杯倒满,阿公一人独饮,同样能品出酒中滋味。阿公唯一的酒友,是住在离阿公的垛木房不到两公里远的陈六七,他也是在山上住了许多年,管理核桃树,放牛,种一点喂鸡的玉米。不论哪家杀鸡或者有什么好吃的都忘不了对方。早上阿公走到陈六七干活处,“老七今晚上来搭我吃酒。”阿公说。“你又整什么?”陈六七问。“杀了个鸡,要来呢嘎。”“去呢,去呢,醉酒咋个能不去。”
晚上两人一起喝酒,说好今晚只喝两杯,但你加一口,我倒一嘴,酒就没有数,也不知道吃了几杯。酒越喝越多,话无边无际,阿婆坐在旁边就着火光纳鞋底,也听两人聊天,时不时也参与其中聊几句。两人觉得该散时,月已挂树梢。
阿公阿婆晚饭后的常态是围坐在火塘边讲话,讲玉米、核桃,讲遇到的一头熊,讲儿孙。讲到困,阿婆就上床睡觉,阿公在火塘边抽旱烟。阿婆一觉醒来,见阿公在火塘边打瞌睡,喊一声“碎米她爹睡觉了。”“哦,咋睡着啦,睡啦!睡啦!”随即上床睡觉,只是几分钟鼾声打破了林中的寂静。
当公路通到核桃树下,开车从家到核桃林只要十几分钟的时间,没有必要住在山里,阿公阿婆回到了村庄,回到了家。现在只有垛木房守着核桃树,核桃树望着垛木房。
图文/张若恒
编辑/杨宏毅
责编/杨宏毅
审稿/张 进
终审/杨凤云
投稿/bcrmtzx@163.com







网友评论文明上网,理性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