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讯副刊】非遗在宾川:甩羊肉粉蒸
甩羊肉粉蒸,我们吃的是文化
丁 强
一直以为我们大理宾川羊肉粉蒸没什么了不起,不管你甩不甩,它都在我们的记忆里。自从羊肉粉蒸被列为大理州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成为非遗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羊肉粉蒸确实了不起,而且到了要大力保护的时候了。而要保护,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多吃。

说到甩羊肉粉蒸,得从我的童年说起。我出生在宾川县古底公社汉邑生产队下队,模模糊糊地记得,我四五岁的时候,家里买了一只黑山羊。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学,主要劳动就是放羊。我没有羊高,力气也没有这只羊大,母亲带着我,我牵着羊去“槽子田”田边放羊,羊拼命要去吃正在收割的豆子,我拼命拽着不让它去。羊瞪了我一眼,一使劲,我摔倒在沟里,我“哇”的大哭了一声就昏过去了。当我醒来,右手疼得要命,母亲把我抱在怀里,正在抚摸着我。随后,母亲背我到对门的七队,请老中医舅姥姥张光浩给我看手,右手从手腕处骨折了。上了夹板,敷了中草药,用一根布带挂在膀子,用中医的方式治疗,两个多月后才好。虽然我对这只羊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但伤好后,还是得继续放羊。

随着我慢慢长大,羊也渐渐长大、长肥,至少有80斤。二姐要出嫁到七队了。那时候依然是大集体,一家人一年最多只杀得起一头猪,没有太多的肉。父母说猪肉不够,要杀这只羊办客。我本来是十分恨这只羊的,很希望它哪天死了才好,但现在要杀吃它了,反倒又舍不得了,毕竟和它天天在一起,有感情了。但为了风风光光地把二姐嫁出去,我同意了。二姐出嫁前一天,父母喊回在村里上门的大哥、二哥和相帮弟兄一起杀羊,我在一边围观,既有点伤心又希望羊快点死,好让我赶紧甩上羊肉。
大人们在一块空地上挖了个坑,架上大锅,然后把装满羊肉的大木甑子放进锅里蒸。那时是冬天,半个多钟头后,甑子里就冒出了白气、香气。到了天即将黑的时候,甑子边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打开甑盖,抓了一根羊骨棒,太烫了。我把羊骨棒左手颠倒右手,右手又颠倒左手,来回这么几次,羊骨棒稍微冷点了,我就贪狼地开始啃,上面有羊肉、羊油、茴香、花椒、辣椒,又香又肥又麻,太好吃了!40多年过去了,今天回想起来依然想淌口水。

这是我第一次甩羊肉粉蒸,也是记忆最深刻的一次。后来家里又买了3只绵羊:一只公羊、一只母羊、一只小羊,随着羊群不断发展壮大,最多的时候有7只,我的地位也提高了,成了村里有名的羊倌、家里的半个劳动力。不杀羊的时候,父母可以剪羊毛用来擀毡条当床上用品,杀羊的时候对全家又是肉食的贡献。我到古底街上初中后,放羊的轻松活移交给了弟弟,慢慢也就脱离了羊群。但有了这么多羊,吃羊肉、甩羊肉粉蒸就成了稀松平常的事,一年吃一次,甚至两次都不稀奇。一般是要家里盖房子,或者结婚这样的大喜事才杀,偶尔也在杀年猪的时候同时杀一只。记得三哥结婚的时候,又杀了一只大肥羊,我依然是颠着羊骨棒从汉邑村到古底中学,一边小跑一边啃羊骨棒。差不多要到学校,就把羊骨棒往天空一甩,羊骨棒旋转着向豆田飞去,感觉飞出了雄鹰的姿态……

后来离开家乡到昆明打拼,甩羊肉粉蒸的机会少了,但也不是没有,有一次到上沧村过年也遇上了宰羊,有两点和我们村不同:一是蒸羊肉粉蒸的锅灶鸟枪换炮,烟囱像炮管直射天空,这阵势有点像打仗,甩羊肉粉蒸更有仪式感;二是他们吃生羊血,我刚开始不敢动筷子。至于羊肉粉蒸的味道也和我们汉邑村差不多。开吃了,羊肉粉蒸是主菜,酒是自酿包谷酒,管够、管饱,但不要喝醉。

这种阵仗今年大年初二在二姐家过春节再次上演。过去杀羊,羊皮是要剥下来拿去做羊皮褂穿在身上,可暖和、时髦了,完全可以当大衣穿,冬天夜晚穿着去理水浇灌庄稼,简直就是一种享受,比不穿羊皮褂的人经得起冷,熬得起夜。现在羊皮基本不剥了,也没有人缝羊皮褂了,直接在火上烧,然后砍成一坨一坨的羊肉蒸粉蒸肉。过去烧羊头、蹄,用木柴,现在改用液化气了,感觉没有了树木的清香。但粉蒸羊肉依然好甩。

父母长眠在水槽子,与日月同辉,和青松长伴。大年初三我们一大家子去给祖先、父母扫墓。父母一共生育了10个孩子,养大成人了8个,到如今,除了父母和二哥去世之外,我们7兄妹都还健在,而且身体一个比一个好。我想,这与我们时常能吃到羊肉粉蒸是分不开的。现在我们这个大家庭已经发展到几十口人了,父母留下来蒸羊肉粉蒸的厨艺家家都会,二姐家一直在延续养羊、吃羊肉粉蒸的传统。今年,所有的羊都杀吃光了,二姐夫说:“还是要再养几个,要不然以后就吃不着羊肉粉蒸了。”


这话我赞成,特别是当羊肉粉蒸都成为非遗之后,更应该继续养羊,继续甩羊肉粉蒸。这种传承单靠几家在牛井坝子的羊肉粉蒸馆是不行的,得有群众基础,最好是家家户户都养羊,会做羊肉粉蒸。我在朋友圈转发新闻时说:“宾川粉蒸羊肉都升格为州级非遗了!下次再有机会吃,要斯文点,细嚼慢咽了。不能再说甩了,因为我们吃的文化,不是甩粉蒸羊肉了!”
作者/丁 强
编辑配图/杨宏毅
审稿/刘 灿
终审/杨凤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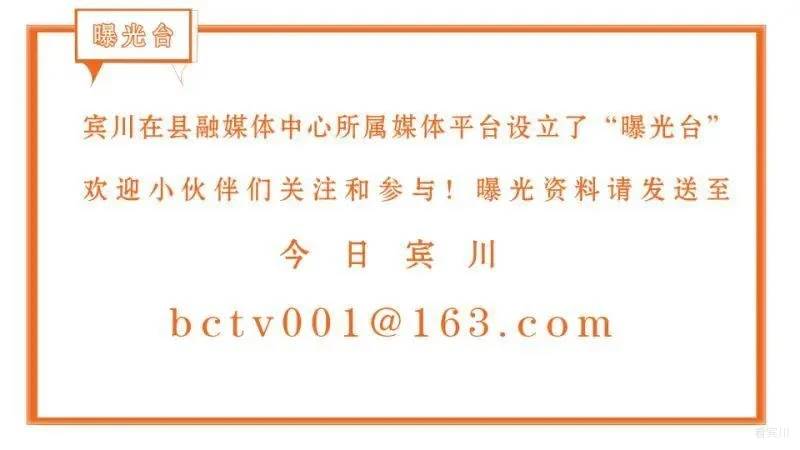



网友评论文明上网,理性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