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川时讯•副刊】烟 缘(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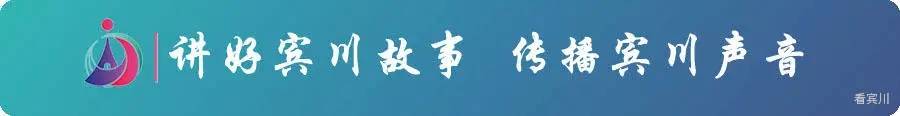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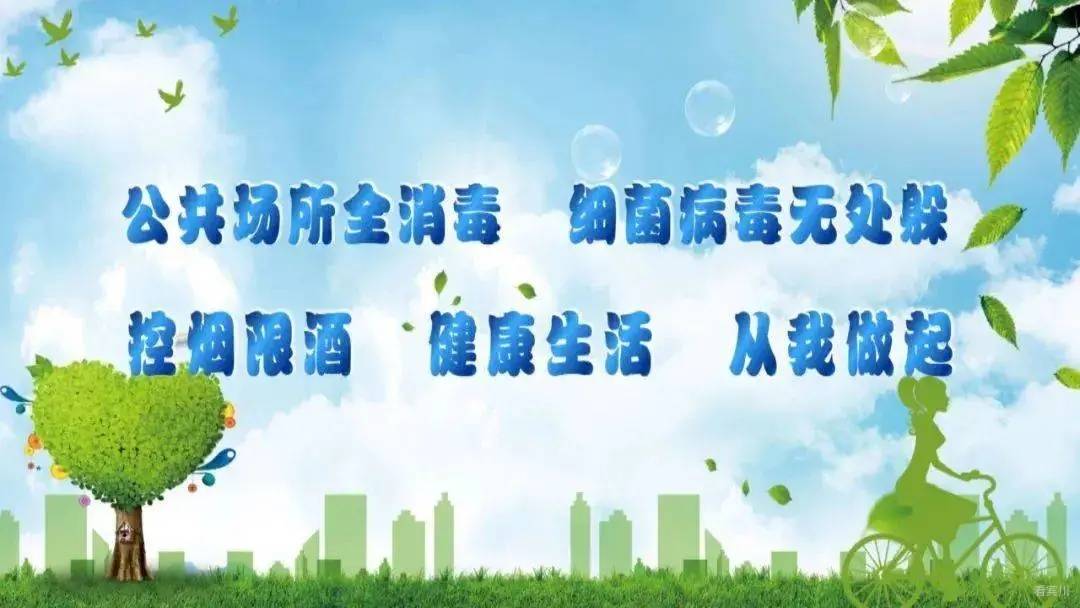


烟 缘
赵思良
回老家的路边上,有几墒烤烟,长势一直不错,主人也比较尽心尽力,视如宝贝一般。从大田移栽、中耕管护到成熟采收,4个多月时间,每一次路过我都愿意驻足片时,为这些黄金叶片的成长留影存念。
我虽然不抽烟,但和烤烟缘分匪浅。成长于上世纪80—90年代的云南人,如果没有参与过烤烟生产,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农村来的。

关于吸烟对身体健康的危害,关于香烟在人与社会微妙关系中的作用,关于烟草对地方产业经济的地位和贡献,实在太复杂太高端,不是我辈所能尽知的。作为一介烟农,最切身的联系是,种3亩烤烟,一家老小全年的幸福生活就全从这里支取了。
1980年初的山区农村,农民刚刚从集体手中获得了土地的经营管理权,虽然饥色尚未褪尽,但温饱的希望已经遍地萌芽。某天,听到父亲向人夸耀,山地里种的小米获得了丰收,全部换成大米,加上水稻的收成,除去应缴公粮,全年都可以吃大米饭,不必再掺包谷面了。小孩子不懂,但可以感觉到,这是一个小农家庭的历史转折性大事件。

有一年春节后不久,乡上给我们村派来了一个工作队员,挨家挨户动员种植一种神奇的农作物——烤烟,说是可以带来更好的经济收入,比种包谷水稻划算。新鲜事物,谁也没有见过,村民都是好奇围观的多,应者寥寥。因为有了当年吃大米饭可以不掺包谷面的底气,我们家和堂哥家、邻居杨兵家半推半就的报了名,小面积试试看,一不小心竟成了整个生产队第一个吃螃蟹的英雄。
亦幻亦真脱贫梦,稀里糊涂种烤烟,烟科员就是全村的男神,说的任何一句话都饱含无尽的科学道理,以及那未知且诱人的发财梦。
既然是发财梦,肯定得倾注最大的热情、最多的汗水,也能收获最多的奇闻趣事。

育烟苗的苗床,用的是往年水稻育秧最好的田块,水肥充足,堆捂熟透的圈粪,用筛粉子面的筛子细细筛过、铺平,再盖上一层松毛,一天浇水两次,感觉伺候月子也不过如此。建烤房,既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抬石头砌房基,挖土舂墙,割茅草盖房顶,砍木料撘烟架,拓土基砌烤龙,一分钱不花,几家人总动员大会战,短时间内硬是在院子里搞成了一个半似碉楼半似畜厩的大家伙。作为一个尚未入学的孩子,我有幸全程参与了以上所有的工作,虽无大功,却也有满满的荣誉感,就如拔萝卜队伍里的那只小松鼠,足以满村子炫耀了。

烤烟属旱作,大田移栽当然舍不得占用水稻田。3公里外大地窝子的3亩陡坡地,当年曾因种植小米解决了全家吃大米饭问题而立下大功,如今再次被赋予重任。皮厂高温少雨,缺水严重,得在头场雨到来之前,早早的就在坡地上打好干塘窝子,及时收集雨水做定根水,雨后立即全家总动员,一天之内全部完成移栽,然后每天一次到山箐里挑水保苗,开始新一轮伺候月子式的劳作。

红

花大金元植株高大,叶片宽展,在水肥充足的地块可以长到两米多高,中耕管理封顶抹芽都极不便,好在地块坡度大,站在上坡方向操作即可;其实,对于烤烟来说,肥大绝非好事,含氮高,叶片过绿,不褪黄,俗称“憨烟”,烤不出高品级的成品。最初几年没有任何经验,我们的辛勤劳作经常换来这样一些老憨烟,付出越多,损失越大。事实证明,减肥更有利健康,金黄才是收获的颜色。


绑烟叶用的小烟杆,是临时到山上砍的,1.5米的黄荆条木棍或稍直一点的火柴头都可以,拔来山草搓成草绳,简单,实用,只要能把烟叶绑起来烘烤就行;对于那种叶柄粗大肥壮的,不易脱水烤干,就用一种特制的武器,在小木条上固定一颗钉子,挑出需要特殊处理的烟叶,在叶柄上拉开几道口子,再肥大的烟叶也能烤干。


记得当时烟站收购烟叶,只分6个等级,一级品每斤可以卖到2块8角钱,末级烟每斤只能卖1角5分钱。交售前的分级定档这种技术难度高的工作,就交给母亲一个人完成了。烟叶出炉不易,母亲会认真的把每一片烟叶抹平铺展开,整整齐齐的码好,规规矩矩的扎把;对于局部有斑点的叶片,她会用剪刀小心的把残损部分剪去,以便跻身上一个等级,比她平时纳鞋垫更仔细,比我们老师批改作业更认真。那些修剪下来的边角料、排不上等级的残次品,也被母亲用菜刀细细的切成烟丝,在农闲时候背到皮厂街的偏坡地摊上论碗售卖,5分钱一大土碗,足可以装几十旱烟锅了,那些烟瘾奇大的山里老汉,都反映说比老品种旱烟展劲。

因种植数量少,乡上并没有设烟叶收购站点,交售烟叶需要背到30公里外的平川街,同样由比老黄牛能干的母亲完成。第一次卖烟,得了几十元的一笔巨款,买了一盏马灯,替换了墨水瓶改造的煤油灯,还买了一个干湿温度计、一架闹钟,都是烤烟生产的必需品;剩余的钱被压在了那个父母当年的嫁妆、金库红漆木箱的最底层,等于是给全家生活充上了电。那盏马灯、灯座的商标及使用说明书,让学前的我认识了不少字。

烤烟烘烤是大活计,费柴火耗时间。煤炭贵,很舍不得用,主要是烧上一年的烟株秸秆和开荒地淘回来的栎树疙瘩。有一次,我得了一个拳头大的皮球,独自在院子里玩,练习投篮却找不着合适的篮筐,很自然的就瞄上了烤房上正在冒烟的烟囱。那年的烤烟季,我并没有因失去一件心爱的玩具痛心惋惜,而是在做了坏事的自责和冒险刺激交织的复杂感受中,尽力当好一个严守秘密的演员;而父亲则多次埋怨栎树柴疙瘩没有晒干,点不着,烟囱不拉风,闷灶。直到年底农闲时候,他彻底清理了烤房的烧火排烟系统,滚出来一个黑不溜秋的皮球帮他破了大案:从烟囱里穿越而来的,不一定是圣诞老人的礼物,有可能是家有小神兽。
三十多元的第一桶金,算是把我家引上了烤烟生产的正轨。此后几年,最初合伙试点的几家逐步分户单干,各自建起了自家的烤房、扩大了种植面积,烤烟种植、烘烤技术也逐步提高了。村里的烟农多了,家家种烟,每到采收季节,相邻几家都有意错开采叶、绑烟、装窑、出窑各个环节,互相委工帮忙,大集体劳动时的欢声笑语便轮流着在各家小院里回荡,夜夜不息。

劳动是光荣的,在烤烟生产的劳动中,收获的不仅仅是几十元的生活费,更有无价的人生财富。我可以背着满满的一大竹篮新采的烟叶,光着长老茧的脚板在大雨中奔跑;可以配合老爸在高高的烤房上修补茅草房顶,可以下厨做饭招待前来帮忙的邻居亲友,放学后第一时间冲到烟地里除草。当一个合格的烟农,汗水无根,其乐无穷。
因耪烤烟占用了粮食面积,随着我们兄妹三人渐渐长大,一个问题必须解决:耕地。初中毕业那年暑假,在山区村小学当代课老师的大哥领导下,我们哥俩在村子东南方向的赵家坟坪山上选址圈了一块约4亩的荒地,此处离村子较远,骑骡子需要走40多分钟。这块地虽然地势稍平,但土层较浅,乱石奇多,垦荒工作极其艰苦。兄弟开荒,在一年中最热的40多天里,我们哥俩洒下了一生中最多的汗水,晒褪了最毒的太阳,徒手挖掘、搬运了最多的土方乱石和老树疙瘩,吃了最多的冷盒饭。新垦的生地为全家提供了充足的杂粮,让种烤烟的熟地可以继续承担发展家庭支柱产业的重任。

除了扩大面积开荒,对老熟地进行土壤改良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好方法。读高中时的一年寒假,老爸买了一把超大超重的十字镐,交给我一个任务,说是大地窝子的那块地,因为连续多年种烤烟,耕作层越来越浅,不保水,烤烟越来越难耪了,让我把整块地深翻一遍。我不辱使命,每天早出晚归,用一个月时间,硬是把整块地半米深的石块、老树疙瘩及生土全都翻了出来晒起,还在离家较近的承包地里挖了两个小水窖。第二年的烤烟长势超常的好,但大部分都长成了老憨烟,废了;又因为耕作土层较厚,一场透雨过后,一块地就变成了烂泥坑,把全家人搞得苦笑不得。
其实,情商较高的老爸本意是让我体会一下农民的艰辛不易,从而好好读书另寻出路。但我收获的经验却与他的初衷严重不符:一是十字镐还是重一点的好使;二是耪烤烟不能图表面的高大上,得综合考虑均衡营养;三是当农民也得有知识。

时光倏然而过,家里连续种烟19年,基本伴随我读书求学过程始终,直至我作为家里唯一的大学生最后一个离开校园。因自然条件差、技术落后、家庭劳力不济等各种原因所限,我家种的烤烟从来没有超过4亩,年收入也始终没有过万,耪烟已然成了食之无肉弃之有味的鸡肋,却实实在在为我们兄妹几人的成长充电输血19年,称之为家庭一号功臣应该是实至名归。

已经整整20年不种烤烟了,我们兄妹几人各有所求,各有所就,各奔东西,都离开了老家,当年辛勤开垦的山地早已退耕成林了,其他地块或退耕,或委托亲友代管,早已走出了我们的生活,走进了记忆。而当年比老黄牛还能干的老爸老妈,古稀之年不再农事劳作,但依然倔强的坚守空巢,守望着我们共同的记忆。

往事如烟,烤烟亦如烟。和谐社会,健康生活,全民戒烟,抽烟的人越来越少了。单位后院的专用吸烟区,两个戒烟困难户、钉子户同事在喷云吐雾,并自嘲哥抽的不是香烟,是寂寞。他们似幻似仙的烟雾缭绕中,也应该有我当年流下的汗水,泪水,以及有趣的故事。
图文/赵思良
编辑配图/杨宏毅
审稿/吴洪彪
终审/杨凤云


网友评论文明上网,理性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