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川时讯•文化周刊】忆儿时卖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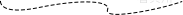
段家才
井水清凉亦卖钱,重游故地忆童年。
一分一饮解焦渴,共用山瓢不弃嫌。
村北椿阴一担开,遥观企盼路人来。
几分散币入衣袋,心意融融现两腮。

炎热的夏日阳光、浓密清凉的树阴,打开了记忆的阀门,将我拉进时间的旋涡,眼前的光景渐渐倒退,晃然间我又回到了童年的老家。

儿时家贫,六七岁开始,我就想法子挣钱,少到几分钱,多到几角钱。印象最深的是卖饮水。
故村力角总府庄紧靠祥宁公路,路两边都有人家。沿路往北六里是永胜县片角街,是离我村最近的集市。小时候,记得这条街每隔四天到第五天赶集一次,乡人称为“空四赶五”。长大后知道它是按西历日期赶集,每月号数个位3、8的日子赶集,大多数时候是五天一次。
上小学之前,我主要干的活是放家里的猪、牛、驴。猪少时有三四头,多时到十几头近二十头,家里用养猪卖钱支付生活用度;牛有一头,用来耕地;驴有一头,用来驮物。平日里,早饭后放牲畜要到下午三点左右才回家。夏季片角街赶集日,放到一点左右就回家了。

午后,祥宁路两边村子里去赶集的人陆续走在了回家路上。太阳火辣辣的,可以看到近地面空气里有波纹状腾腾上升的水蒸汽,花草树木干渴得卷起了叶子。我从家中井里打了水,倒入两只小桶,放上一把瓠瓢,搭上竹扁旦,戴一顶旧篾帽,沿公路向北挑约1里,路边有一棵高大的老椿树。那时身小力弱,挑不了太多水,每只桶里约半桶水。把两桶水并作一桶,放在路边的树阴下,盖上篾帽以遮挡灰尘,就算摆摊了,开始卖水了。在儿时想象中,这棵老椿树就像上天在这里撑开的一把大伞,又像一所天造地设的房子。长大之后,非常怀念这棵树,可惜2004年整修祥宁路时,被砍掉了。那天回村,到了那里,看到原来老椿位置附近一棵有几分像老椿长得郁郁葱葱的大皮杨柳。爱屋及乌,带着对老椿的怀念,我拍下了这棵大皮杨柳。


那时,祥宁路虽是土路,但是车辆很少,灰尘也就非常少。一分钱喝一次水,管客人喝够,叫“一分钱一饱”。一天卖水一两小时。有时能卖五六分钱,有时一个买水喝的路人也碰不上。能卖到一角钱那天,就会心花怒放了。上小学之前,有人会到村里卖冰棒,三四分钱可以买一个。几次卖水的钱攒起来,可以买个小玩具。有时把攒的钱交给母亲,让她添上些钱,给我买双塑料凉鞋。有时母亲给家里买一样急用的东西不够几分或一两角钱,会跟我“借”。说是“借”,而往往就是添补家用了,我也没跟母亲要过。上学之后,五六分钱可以买一本小楷本或算术本。

为什么不在我村靠路的村口卖水呢?因为村北那些位于田野里的路上最热,路人干渴之后喝水的欲念非常强烈。若路人到了我村,村后不远的村子里的人可能就舍不得花钱买水喝了,再熬一阵子就到家了。那时大家都很穷,不轻易花一分钱。再有,若路人到了我村,遇到熟人,熟人家在路边,他可能去熟人家讨水喝,不会买水了。用今天的话说,这可以叫“寻找商机”。

我是一个过了许多艰苦日子的人,所以一直以来都惯于过一种简朴的生活。我所在的宾川县是云南省年降雨量最少的县级行政区域,干旱少雨,几乎十年九旱。一遇干旱年景,粮食欠收非常严重,乡亲们常说:“海簸才抬上楼就没有米了。”海簸是当时农家用来收打稻谷的竹器,体积比较大。平日里放在楼上,用于装粮食或其他东西。稻谷收割季节,把它抬下来。稻谷收完了,就要把它抬到楼上去,用它装粮食。我家经常是米和包谷等粮食都欠缺,需要去借粮。所以,直到现在,一看到粮食浪费现象,我就感到非常痛心。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十分注意教育孩子力戒奢侈,谨身节用,他的警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已成为世人传诵的名言。在其教育下,儿子司马康从小懂得俭朴的重要性,以俭朴自律。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到一些年轻人总是怕苦怕累,读书嫌苦,干家务也嫌苦,而享受东西,却总想要好的。说说我们年少时的苦日子,忆苦思甜,以此自免自励,让年轻人看看我们过去的日子,或许对他们会有所触动。

现在,我们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了,生活宽裕。但是,仍然需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厉行节约,才能让现在丰衣足食的日子长久。
作者/段家才
编辑/杨宏毅
审稿/吴洪彪
终审/杨凤云
投稿邮箱/bcrmtzx@163.com


网友评论文明上网,理性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