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川时讯•文化周刊】从皮厂到平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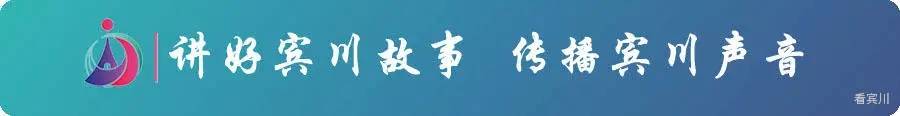



•赵思良•
从皮厂到平川,幼时那是到外婆家的距离;稍长,是寒门学子到平川地区最高学府的距离;现在,是一段乡愁的距离。
从皮厂到平川,是从一个山区小村到一个山区小镇,被钟英分成均等的两段,约30公里山路,40分钟车程,步行随心所欲。

平川地区三乡一镇,偏居宾川县东北一隅,是全县高寒、偏远、贫穷的代表。平川不只是平川人的平川,是整个片区三乡一镇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交通枢纽,赶平川街,读宾川二中,便是三乡一镇共4万多人最平常的生活、最高的人生追求。这是20年以前的情况,2005年,原古底乡整建制并入平川镇,消失在历史中;2012年,建校整70年的宾川二中拆并停办,成为六千多学子永恒的回忆。

回忆,是在不惑之年的人生期中总结和怀旧情感寄托,也是为今后的人生加油充电、继续前行的理由。


1990年仲夏,燥热的皮厂村出了两条比天气还热的大新闻:第一条是我小学毕业,以钟英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本乡的初级中学;轰动全村的一条是本村的李育周从宾川二中毕业,考上了云南工学院,成了村民争相传告的大鸡枞。那一年暑假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无论是上山放牛,下地除草,回家做饭,我都沉浸在村民赞誉的幸福中和对自己远大前程的憧憬中:3年以后,我也要考起宾川二中,去那神奇的平川观音寺读书;6年以后,我也一定能考起云南工学院,成为我们村一朵耀眼的大鸡枞。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常常在你不经意间打个折扣。1998年9月我考起云南工业大学(云南工学院后身,现昆明理工大学),李育周来昆明西站接我的时候,他已经大学毕业并在昆明工作4年了。我的三年规划、六年梦想在八年后才拼拼凑凑磕磕拌拌的上桌,大鸡枞变成了干巴菌。

时间还得重新穿越回去,现实虽然很骨感,但远比理想精彩得多。
我的二中梦是从钟英初级中学开始的。李育周在二中给我树立了标杆,但我必须从钟英中学起步。


这是一所隐映在一大片松树林里的学校,松风阵阵,书声朗朗。如诗如画的背后,是那个年代贫困山区贫困学生的集体写真。在这里读书的几年里,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一是做饭,二是坐车,三是做贼,四是做梦。学校里有高低木架床那种小号宿舍,只有女生才可享用,男生全部挤住在一间大教室里,通铺,直接在楼板上铺上草席及被褥即成。各人的床头都放着自己的百宝箱,木箱基本都是父母甚至祖父母的嫁妆,藏品是大米、小米、包谷面、老南瓜、洋芋、洋丝瓜、四季豆、酸腌菜、盐巴、腊油。百米以外有两间被柴火熏得像山神庙似的平房,男女生各占一间,一排一排的整齐排列着红泥巴糊成的土灶,这便是学生集体厨房。每天早晚两次,下课铃声响过,上百口土灶同时起火,上百套锅碗瓢盆同时交响,此情此景,何其壮观!那时候食用油很珍贵,一日两餐是没有荤菜和炒菜的,蚕豆大的一颗腊油炼化后,冲上满满一锅冷水,烧开,各种瓜菜下锅,再烧开的时候,另一边铜锣锅里的米汤刚刚退去,饕餮盛宴便开始了;往往是吃到最后一碗锅巴饭,才是熟的。课余时间也很珍贵,所以把厨房当成了赛场和战场,曾做过一次测试,从打铃下课奔出教室开始计时,淘米洗菜劈柴烧火,到饭罢收洗结束,在操场边靠着老松树晒太阳剔牙齿,32分钟。

坐车?其实很少有车坐。同学里其他四山头村里来的,交通基本靠走,条件好的可以骑毛驴、骑骡子。皮厂人有福气。金沙江边有煤矿,每天都有几辆拉煤车进出,铁牛55,丰收35,东风大卡,解放大卡,茶花双排座,蚂蚱头弹弓叉(手扶式),屈指可数的几辆车,我们在几里以外便可听出是谁来了。偶尔碰上,好心的司机都会停下来,任由学生娃以及随身背着粗粮瓜菜的竹篮,插筷子似的插在煤堆上,一路颠簸摇晃,一路欢声笑语,在烈日和灰尘及拖拉机的浓烟中蜗速前进。作为回报,男生会在半路有水塘的地方,自告奋勇的跳下车,拿着皮桶,给喘着粗气的拖拉机加水降温,而司机则可以高坐驾驶棚,点上一支金沙江牌带把烟,眯上小眼,幸福的享受着小喽啰们的服务,那表情实在是帅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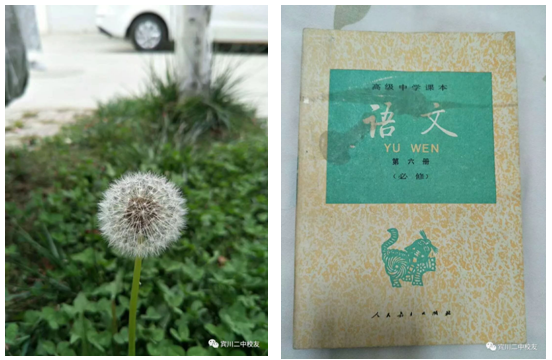
关于做贼的经历,在近30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居然没有一丝愧疚和自责。我们袭击的目标,主要是柴禾和蔬菜。每周一次从家里带来的东西有限,除了主粮和洋芋,其他时鲜菜蔬难保存,经常断货,不足部分就得靠智取了。教学楼后边的松树林里,每一棵树下都堆放着一堆柴禾,权属分明。松树林既是柴房,也是我们取之不尽的柴禾基地,把松树上的干松枝、松球扳下来,便是最好的燃料。不过,十二三岁的意识里,别人的劳动成果似乎更有价值,于是,我的柴堆便是你的柴堆,你的柴堆也是我的柴堆,每天早上都会发现,各柴堆的高度会变戏法似的此消彼长,柴堆外的朋友关系、同学之谊依然坚如磐石。树林里的空地上,有自办伙食的老师会辟出几尺菜地,耕作的过程都会有自告奋勇的学生热情参与,也培养了许多家贼。有一次,初三班的一个师哥业务不精,趁着月色把班主任老师菜地里留着的茄种给卸了,招来的不是责罚和批评,而是善意的嘲笑:圆胖的茄子已经发黄,籽种已经成熟,还能吃吗?下次应该取身材苗条的、穿着短裙的那种!偷菜是技术活,项目选择很重要。学校周边的村子里,盛产老南瓜和洋丝瓜,产量高,耐储存;还要分析对象,一般选择亲戚、熟人和同学家下手,成功率高,万一被发现了,可能还会有惊喜,主人送的比自己偷的还要丰盛。

物质需求暂时得到满足后,精神追求也偶尔会提到心头:我的生活不应该只停留在钟英垭口内,外边还有平川垭口、松坪哨垭口和其他更拉风的垭口。夏季天气长,下午饭后,借背英语单词之名,沿着土公路一路游耍,采黄萢(一种野生浆果)、找菌子、打蛇、用桉树叶练飞镖,一直来到大垭口(钟英垭口),站在那棵地标式的老清香树下,平川坝子一览无余。平川河横贯南北,在河的中段,与观音寺隔岸相望的,便是我心中的圣地——宾川二中;平川河的尾端,盘口箐山脚的盘谷村,是我常去的外婆家所在。清末民初,在这个旧社会旧农村的旧家庭里,我外公的父辈的众多弟兄中出了一个大官,后来的国民党中将师长——杨如轩将军。杨将军文武兼修,事国至忠,事母至孝,乡情至浓,民望至高,1942年回乡投资兴办了平川中学,70多年来一直被乡民称颂。这一层隔了几代人的关系,被我用天真浪漫的手法嫁接了梦想:我一定能、必须能考上宾川二中,不然对不起祖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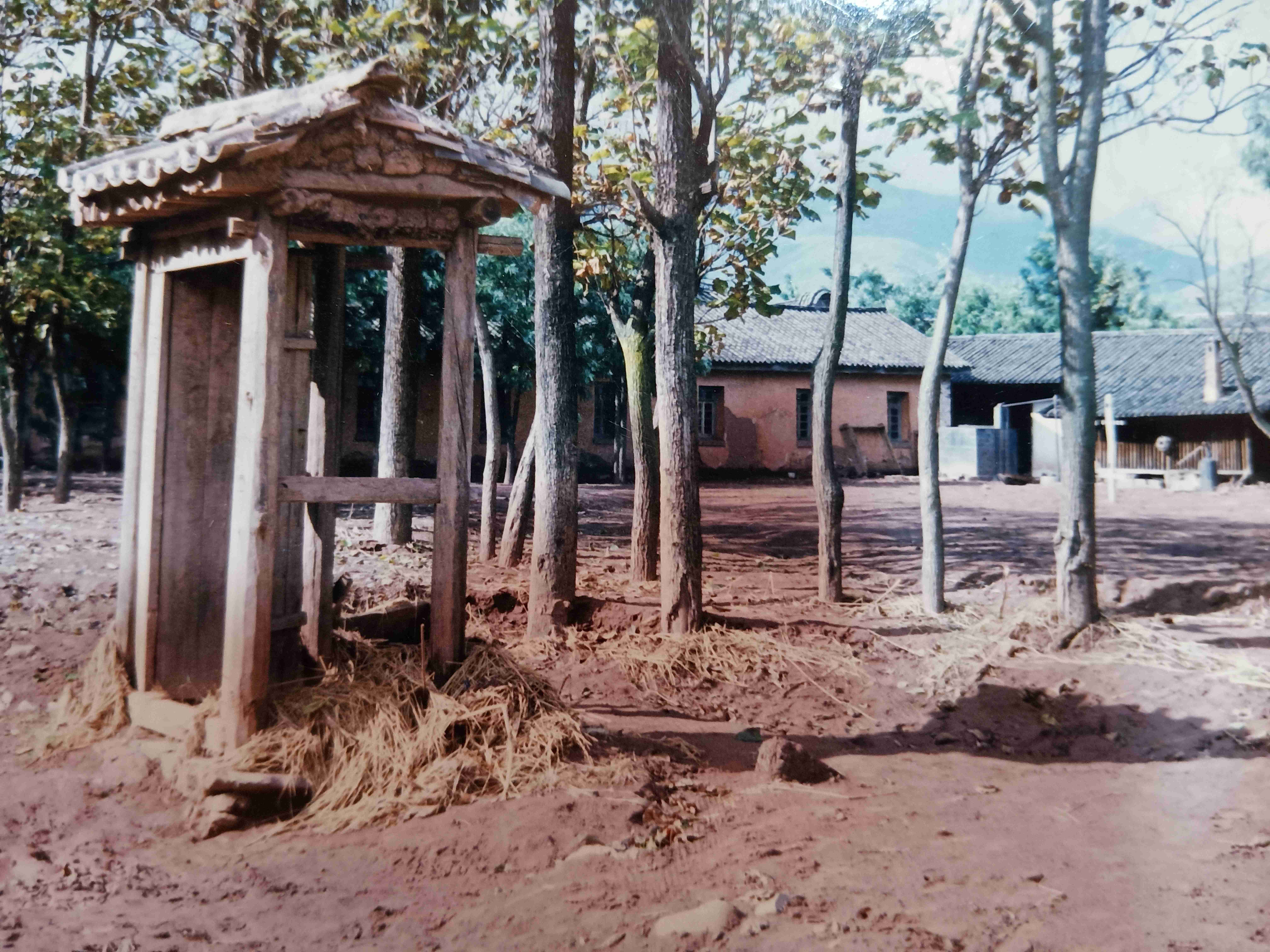
1991年9月中旬的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又来到了大垭口的这棵老清香树下,望着远处被浸泡在一片汪洋沼泽中的二中,怅然若失。几天前的一场山洪大水,把这一所历史名校从物理上彻底毁了,也把我的美梦冲得七零八落,两年后我该去哪里读高中?二中会不会重新建盖起来?那种感受,就如我暗恋了多年的梦中情人突然就被别人领走了。此后几年的时间里,我在师哥们断断续续的介绍中见证了二中的涅槃重生:战洪魔,患难与共师生真情;打游击,借宿街头流离失所;迁新址,三年重建母校新生。经过这一次灾难洗礼,二中精神更加显得耀眼夺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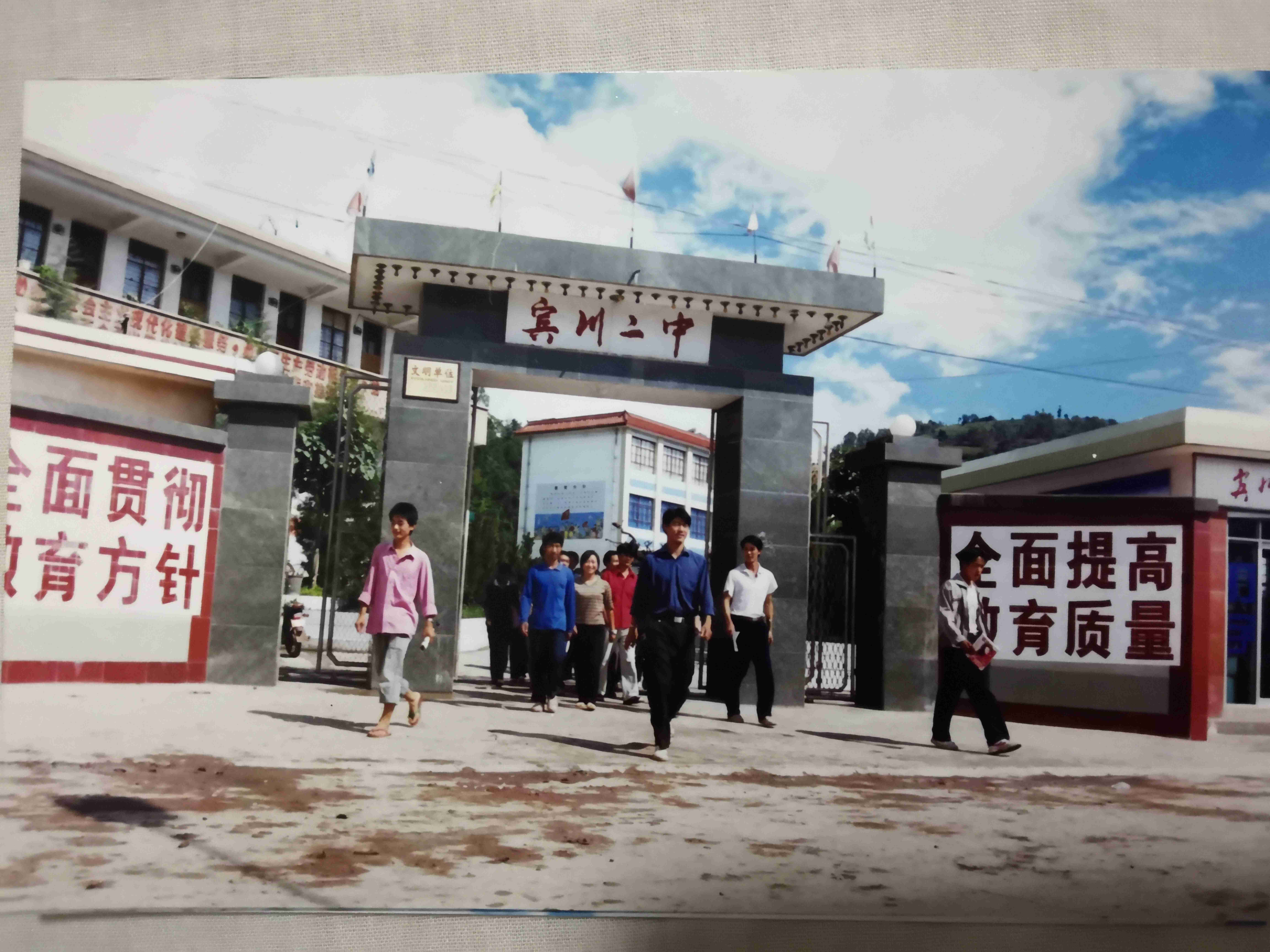
当年小升初的优等生,成了中考落榜生,却因此巧妙避开了去二中居无定所读书的经历。1994年我经过复读终于踉踉跄跄撞进二中的时候,新校区威武雄壮的教学楼已经投入使用,窗明几净的师生宿舍楼还散发着油漆的香味,这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平川街最喷刚的建筑了。站在校友前辈们汗水浇筑的校园里,新生简直就是享福来了。我们对新学校建设的一点贡献,就是拉运煤渣铺填运动场跑道,在学校后边的偏坡上栽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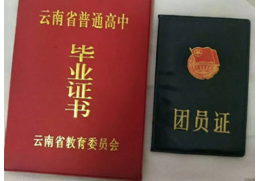

一切都是新的,一切也都稍显不足。在教学楼前尚未平整的土台上,学校为新生举办了迎新晚会,宗克达、宗克仁哥俩的相声《木许传》“小说里有一个好汉叫李鬼,手持两把大爹”让校友们记住了皮厂老表的幽默;文体老师逐集分期放映了录像《乌龙山剿匪记》,收看了当年首播的电视剧《三国演义》第一集。我的二中梦就是在这样的文娱气氛中变为了现实。新鲜之后的平静中,求学生活还是一如既往的鲜活、有趣且艰苦。


高中生,成年了但并不成熟,我们都会有意的让自己尽可能的面对一些困难和挫折,以增加一点关于成长记忆的资本。因为升学率极低,同班同学中,皮厂来的只剩了赵树山、杨武我们3人。家有高中生,对于我们那种山区农村家庭来说,意味着要比其他家庭付出更多。在那几年中,我们三个家庭都开足马力,多种烤烟,多养猪,我们也都还懂事,寒暑两个假期和每个周末,都尽心尽力参与农事劳动,欲跳出农门,必先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皮糙肉厚的农民,和家人互相加压、互相鼓劲。每周一次的来回往返,我们仨都会约齐了结伴出发,在这30公里的山路上艰难的编制着我们的梦。虽然有时也会遇上拉煤的免费拖拉机,并且此时也开通了一路每天一趟票价3元的县乡交通车,但我们还是愿意步行上路,以取经的执着精神煎熬着、享受着属于我们的艰辛或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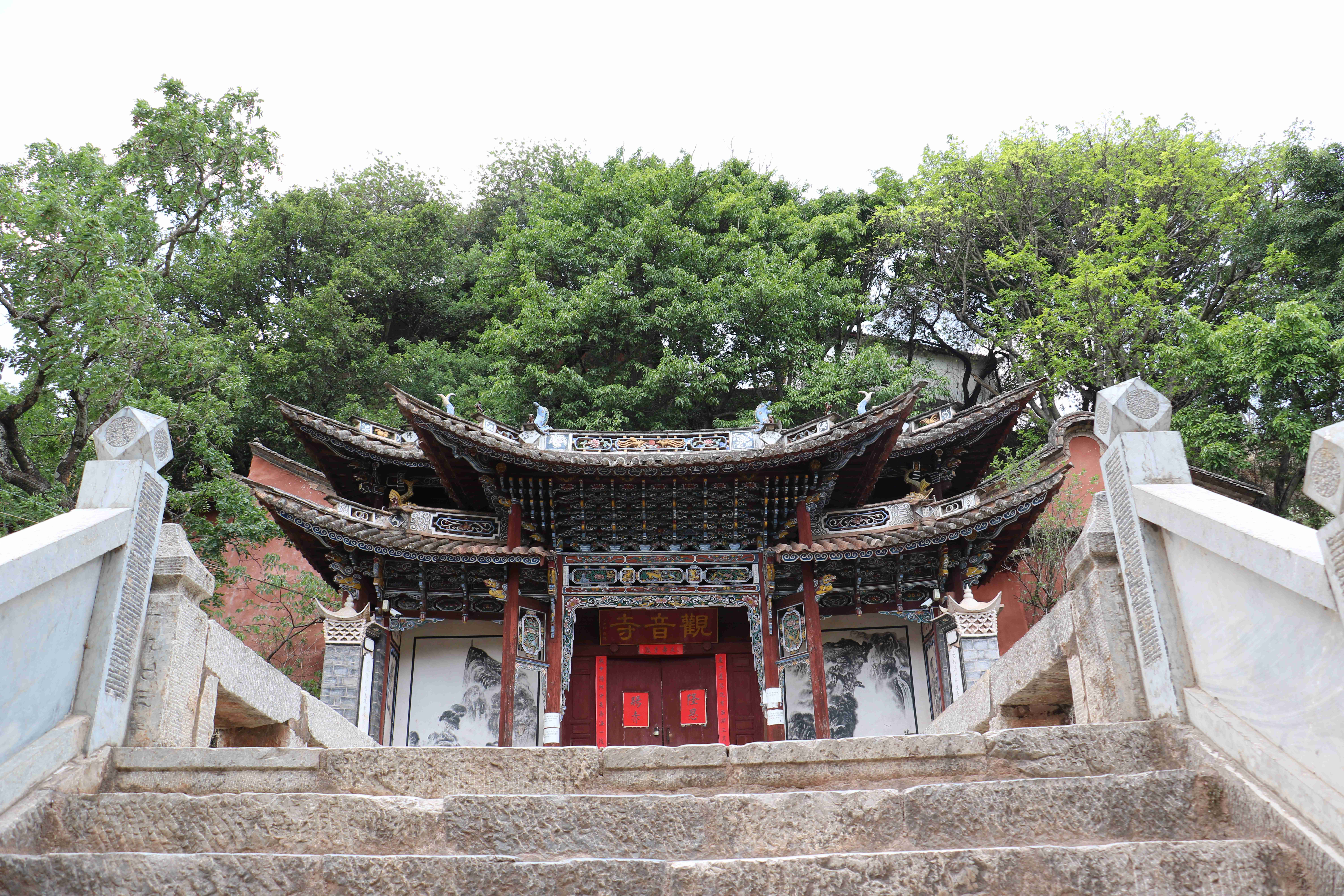

学校自办有食堂,由于水毁重建以后条件所限,每天两顿寡油少盐的青菜洋芋,给正在飙长的身体染上一层菜色。于是,每周回家就像英雄归来,老娘会带着牵挂陪着小心虚寒问暖,老爷子二话不说就磨刀霍霍,院中某只飞鸡便有生命之虞了;驻校期间,如果听说同班同学中哪家杀猪了,立即便会集结大队人马,自行车开道啸聚农舍,以功夫片(回锅肉)为主的各种特色杀猪菜,直吃得个个油光满面,主人心满意足(吃的多,说明主人手艺好,有面子)。宾川人把吃肉叫“甩肉”,生猛霸气,被我们演绎得淋漓尽致。

吃货的乡愁,自带一股葱花味。20年时间转瞬即逝,二中没有了,家乡的一切都变了,当年又傲又倔的小鲜肉,也变成了中年油腻大叔;但这股葱花味却越来越浓,皮厂到平川这段山路越来越清晰:
傲矩清狂出村郎,
忽然不惑竟黯然。
清平慢酌柴米趣,
神游万古不思量。
作者/赵思良
编辑/杨宏毅
审稿/吴洪彪
终审/杨凤云
投稿邮箱/bcrmtzx@163.com


网友评论文明上网,理性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