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川时讯•文化周刊】关年风(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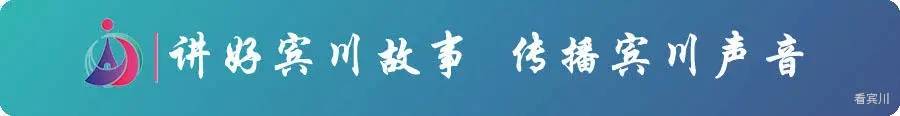



•南 黛•
慢慢地,就对风格外地期待。一种执着地关注。细细碎碎地敏感,不肯与人分享,半丝半毫的商量也没有。最耐得寂寞的,还是冬天的风,是冬天挨近年关的风。褪了春红、褪了夏绿,清清楚楚地张口喘息。大开大阖。
枝干裸露,依稀在苍茫之间。枯枝并没有摧折,砸落在地的是枝杈身上的琐屑。无一例外,枝丫是僵硬的,在风里阵阵颤鸣,走着金属的腔韵和板眼。

越近年关,越捻着季节的骨。四季的力先是灌满了迂回的风,攒足了人们的企望。它将所有献祭给了雪。进得腊月,雪总是会来的,或早或晚,总是下着。她是风的情人,温柔得很。
两盒古树茶,静静地躲在书架旁。自家乡寄来已有半月,还有三天就要过年了。我在心底喟叹。拨通那位前辈的电话,提起其中一盒,沿着青年路往西走。前辈守约,准时出现在巷口。
我迈着小步,不疾不徐。小雪纷洒,刮着小风,所以,伞还扶得住。前辈话语不多,我正好可以接得上。
细雪在继续,地面上积了纵纵横横的银白的冰线。路灯渐次张开欣喜的眼眸,我仰面,和它们一起望着雪幕外的天,是黑的,幽幽的神秘。
街灯,在风中闪着莹莹的青光,像是一枚枚嫩嫩的明星。一条短信过来,是那位前辈:雪压大地如地毯,走来玉人手撑伞。感君高义赠香茗,斗室袅袅尽茶香。
淮河畔的风声脆响,虽是年关,却无鞭炮声声。唯雪意清净。积雪下的冬青木,青青地长着,又孕了半粒大的籽儿。这冬青,长在北方寒地,却活成了春意。

“淮左竹西飞雪夜。晓角清寒,嫩绿鹅黄舞。探入梅林香吐麝。玉人词笔春风忘。”这首五年前填的《蝶恋花》,仍凝有正月十二日的一朵小小雪花。风声押准了文字的行脚,我吹响了北地年关的调子。一个人,仄仄的孤音。
腊月里,什么都在飞逝。飞逝的东西是被风追赶的。是经不住等待的。过年必吃的炒米花,再也不需要筛选上等糯米,进行精蒸揉晒了。街心里就能买到,十五元一斤,红藁汁、蜂腰米。色如新妇颜,态似柳叶眉。经了多少日头,过了多少风色。我嚼不出过去的味。

年夜饭挑着春绿、夏青、秋黄、冬白,一直旋转,旋转得太快,风卷残云。很快,桌旁,椅空无人,新新鲜鲜的饭食。二、三十年前,那只大公鸡,通体雪白,冉冉踱步而来。为了过年能够吃它的肉,每日,母亲都赶它到田间啄虫子贴膘。我便作那贴身侍卫。然而,除夕前一天,大白失踪了,没有跟我打半声招呼,来去如风。
风过洱海。太阳伏在海的背上,从海东走到海西,它就成月亮了。我毕竟看见了。初春风尚寒。海水并不是一种纯碧,有黄的颜色,有绿的颜色,有一线为纯白。那是海鸥栖息在堤埂。
这海鸥背上的白色和灰色好高级啊!女伴赞道。
莫兰迪。脑海中蹦出三个字。嘴里却说道,像天鹅一般高贵,但是,没有疏离感;像鸽子一般平易近人,却又比它优雅。
就是。女伴适时补充,它的尾巴好像燕子。双尾似剪,流线柔和。

洱海其实是湖,却也足够大。沿岸屋舍密集,炊烟、树枝、风声复交纠缠。从来如此。日子好过时,当地人喜欢到洱海边撒欢;日子难过了,当地人更愿意到洱海边走走。心里都知道是为了什么,嘴上都说不出是为了什么。
阳光打滑,全向水面倾斜。波纹蒙蒙,像滴流着彩色水银。立在岸边一隅,暗暗想道:洱海是够阔了。正是宽阔,才生出了这无休止的风吗?人们成年喜欢来此兜风,也正是兜回了这一把或者一捧的风,才吹散了世间人一生中所遇到的忧痛吗?
西风劲吹,家家都掩上柴门。有客来访,但闻犬吠。
正月里,仍是风天,太阳走得快,过屋脊,下台阶,跃过山墙,很快就要从西山顶滚落。
请春客,这风俗就是一个拴风筝的大线轴。从腊月开始,它就一圈圈地转着收拢线端。外村的,外县的,外市甚至外省的亲故,乘着风筝,飘摇举步,赶上日头,坐在堂前。

风色太大,得眯着眼才能看清久别的面容。无论迎风,还是背风都忍不住簌簌发抖。火盆架起来了。柴火鸡的香味四下窜溢。柴火鸡端上桌了,火腿肉就下梁了。火腿肉端上桌了,腊香肠就脱绳了。腊香肠上了桌,蒸肉和“腌参”粉墨登场了。请春客完了,年关尽了,又是一年。

太阳在天上转圈圈,风在地面画圈圈。很快,风吹得人连眯眼望火苗都不能了。大半天功夫,太阳散尽了热。黄昏,它牵着风的手,把人们围进同一屋檐下,眼看着他们变成柔情皎皎的月光。
作者/南黛
编辑配图/杨宏毅
审稿/杨宏毅
终审/杨凤云 吴洪彪
投稿邮箱bcrmtzx@163.com


网友评论文明上网,理性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