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川时讯•文化周刊】大爹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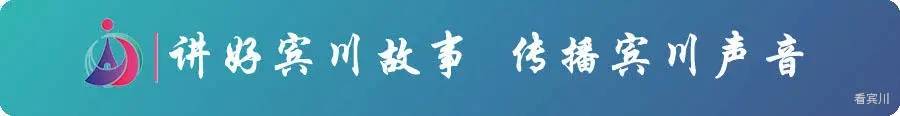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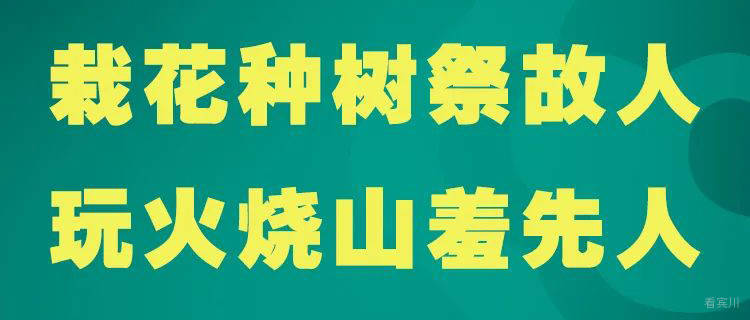


·赵思良
2003年4月初的一天,我收到了皮厂老家大爹寄来的一封信,虽然写的都是他自己的病情已趋平稳,生老病死乃自然现象,让我不要担心牵挂、安心工作之语,但从皱巴巴的信纸和不再刚劲有力的笔迹中,我明显察觉到他的病势已经很沉重了。“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所以很恐怕这事也一律”。果然,两天后,大哥就打电话来,说大爹已经去世了,怕影响我的工作,让家里办完了后事才告诉我。
20年过去了,每至清明,我都会想到以上两件事,不是为未能与大爹最后告别遗憾愧疚,而是对其中的隐隐联系或纯属巧合十分不解,思之愈甚,困惑愈深。

父亲一辈有弟兄四人,大爹是长兄,我父亲是四弟,伯仲叔季文武恒正队列齐整,构成了一个标准的农村家族范式。大爹在解放前当过兵,退伍后回乡当了乡村教师,在皮厂的各种沟沟箐箐梁梁凹凹傈僳族山寨里转悠了一辈子,朵背箐岔箐锁角箐豹子圈大龙潭黄栎水井,地名就透出一种不寒而栗的荒凉,都是那种一师一校三四个年级七八个学生的校点,老师的任务不仅仅是授课,还要给学生取名、剃头、当翻译(傈僳语),给村民调解矛盾,出主意决策重大事项,代笔写信写对联,给办客事的记账挂礼,以及回村时代购物品,和邮递员一起包办了村长的大部分事务。大爹热爱生活,有大山情怀,把如此枯燥乏味的生活经营得有滋有味,也在40多年的山区教书生涯中炼成了当地名师,建立了德高望重的人设。
80年代中期,大爹终于把皮厂村辖内所有山区村小学校点教完了,临近退休的最后3年,经组织关怀,调动工作安排在了皮厂村完小,接手新一届入学新生,班主任兼全科老师。为了能够接受名师大爹的启蒙教育,我推迟了一年入学,46名学生挤在一间四框烂荡八面透风的大教室里,成了大爹这辈子领导过的最大的队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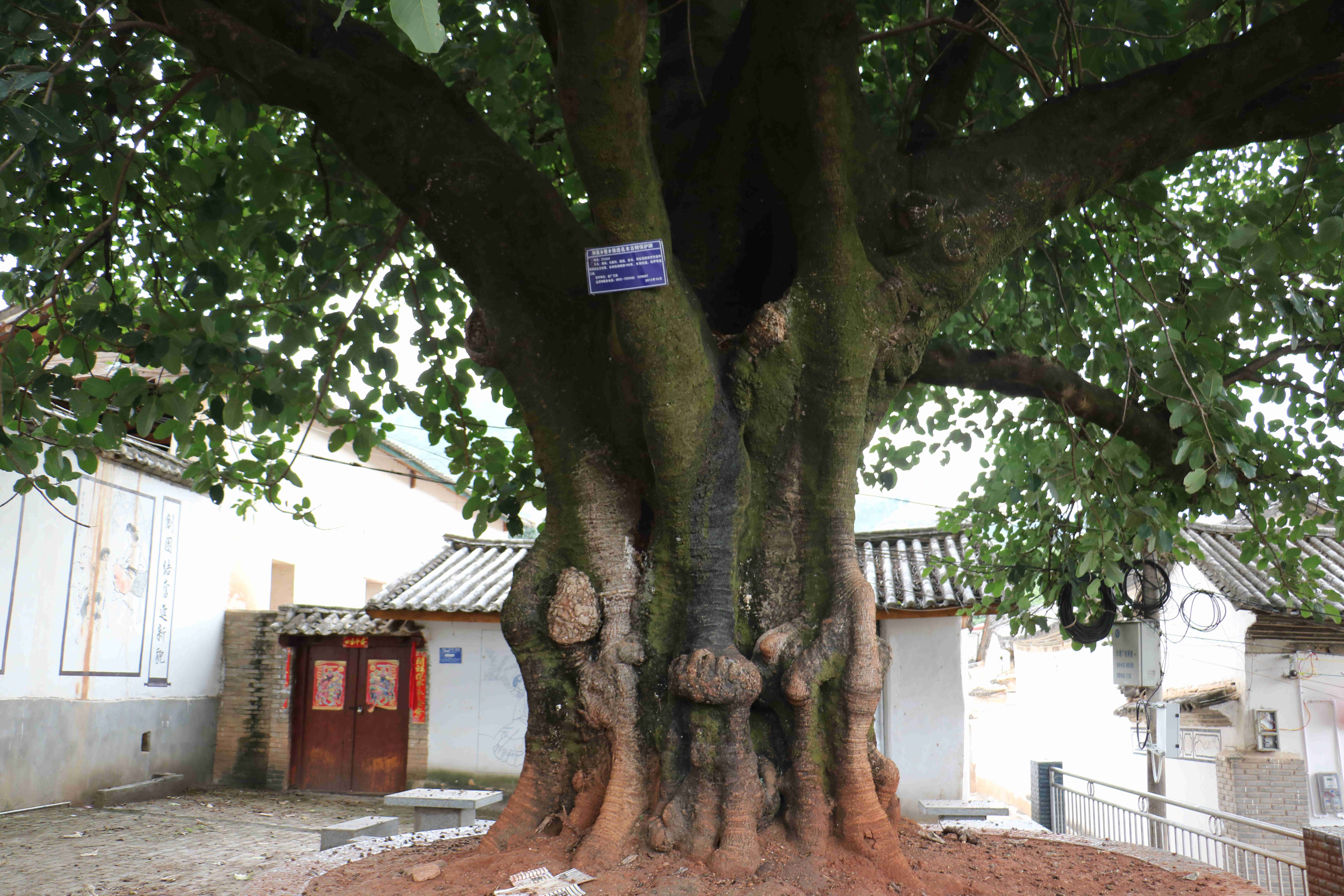
我的开学第一课,是大爹老师给我取学名。那个时候的山区孩子在正式入学前,没有幼儿园学前班的概念,也没有正规的学名,老顺老强老幺丫头,以及巴咪乃哚等傈僳话直译的乳名,虽然比不上闰土那么网红,至少比二狗子要强,乡土气息浓,辨识度极高。为数不多山区村小校点的学生,几乎都是驻校老师帮取的学名,罗富贵余进财张有旺等等,把穷乡僻壤乡亲们向往富足生活的朴素且美好的愿望表达得一览无余。我虽然不识字,但对如此露俗的名字颇不以为然,要雅一点、锋芒不露方好。给亲侄子取名,老教书匠使出了十二分的功力,戴上老花镜对着新华字典作了考古级别的研究,最终拿出的名字虽无大雅深意,但念起来口感还不错,便羞答答的认领下了。
给亲侄子当老师,给名师大爹当学生,既有学习生活上的照应方便,也有旁人眼中怪异的尴尬。成绩好了,说是靠关系给了高分;成绩差了,说是连自己的亲侄子都教不好还当什么老师!授业解惑也需避亲,个子矮小的我被安排在了教室最后一排,和其他4个调皮淘气的大个子共享一条一丈多长的原木条凳。坑凹不平的地面,多动精灵的学生,承包了全班的课堂违纪事件。每当被讲台上精准飞来的粉笔击中的时候,几个学生便开始互相推责是对方晃动大条凳引发纠纷。我是聪明且狡猾的,既是赵老师的亲侄子好学生,也是同桌共凳的好哥们,在每一次争端中都能全身而退,既勺且乖,左右逢源。

一个是祖国的花朵,一个是辛勤的园丁,但走出课堂,我们都只能是地道的农民。放学后,我和大爹共同的任务就是到田间野外割饲草,天天如此风雨无阻,不然家中的耕牛和驴子就要断粮了。简简单单的农活,也能培养锻炼一个人的心性。老人家割草从不挑肥拣瘦,选定一条田埂稳扎稳打的推进,所过之处干净利落,就如他刚给哪个村民剃了头一样赏心悦目;而我则从小练就一身小猫钓鱼的本领,忽东忽西的又要找鸡枞又要捉丁丁猫,把好好的青草地搞成一个车祸现场,折腾一下午却竹篮空空。这时大爹就会及时支援,在天黑之前帮我的竹篮也塞满,以便回村的时候可以获得路遇村民的夸赞。这个家庭作业由老师陪做,似乎并无不妥,和正式的课堂教学一样一天天的促进我成长。
从解放前走来的大爹貌似古董,却并不古板,领导了我们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两次春游,留下了最标准的快乐童年记忆。二年级那次是去金沙江边的沙滩上野炊,条件好的同学带了香肠鸡蛋和汽水,我带的是自家熬制的蔗糖和炒花生,野性大一些的同学竟从沙滩礁石间的水潭里摸出了许多青虾,互不相干的食材混搭成了至今难忘的人间美味。三年级时的那次春游就有些惊心动魄了。46个十岁左右的娃娃,竟然在一老头的带领下,循着放羊打猎的陡峭山路,登上了村后高耸入云的鸡冠山,居高临下俯瞰皮厂全村,甚至可以远看永胜和大姚的山,颇有征服感。在山顶那棵状如伞盖的大清香树下,大爹老师兴致勃勃的给我们讲了鸡冠山“雄鸡从鸡足山飞来,化石为山”的神话传说,皮厂村的历史、村名的由来,名人轶事,以及本村各个家族的发展演进。那天的收获,除了大量小学生作文的素材,便是小朋友们在爬沟过坎跨涧时相互帮扶并分食干粮过程中所体现的集体观念和互助精神。虽然鸡冠山近在皮厂村咫尺,全村抬头可见,但由于路太难走,我至今没有再次到过山顶,到此一游恐怕要成绝版记忆了。

46名初启蒙的学生,年届花甲的老师,也许是皮厂完小校史上最大的班级,也是最大年龄差的团队。作为职业生涯的收官之作,大爹在我们班倾注了最多的精力心血,除了基本的课业教学,更在学生的人格培养、社会适应能力方面谆谆教诲,甚至是苦口婆心唠唠叨叨。如果有教过的学生在社会上犯了错误,那将是对老师的极大侮辱。这种情况在多年以后尤显得突出,学生们长大后步入社会,每以“我是赵武老师的学生”互亮身份,立增亲近感,必能获得他人高看一格,人品定然也不差;如果能有幸加上一句“赵武老师是我大爹”,那就更牛了,满分!可惜我并没有享受过如此虚荣,大爹不让。
在皮厂完小的三年,感觉大爹的苍老速度明显加快了,尤其是老赵家遗传性的老年耳聋耳背,严重影响了教学活动。有好几次我发现,在学生自习或做作业的时候,他居然在靠窗的椅子上睡着了,还发出了很响的鼾声。大爹累了。他热爱教书,并从中获得了许许多多的荣誉,知足;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亲自启蒙的小侄子学习成绩还一直不错,有时候甚至到了自我膨胀的地步。在光荣退休的客宴上,他给我送了一件礼物,一本崭新的日记本,扉页上写了8个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秒懂。
幸福的退休生活,比高价养生更重要的,是淡雅的养心,做一个安静的帅老头。大爹一直与本村的邮递员交往甚密,从那里可以第一时间获得他自己订阅的《老年报》和给我订的《小学生学习报》及其他读物,更重要的是可以继续了解掌握他曾经教过书的山寨村民情况,商量着帮忙办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而他那些以前交好的少数民族老庚亲家们,也会在下山赶皮厂街的时候,到家中来坐坐,吃一杯酽得发苦的火烧盐巴茶,让老教书匠兼剃头匠给他们剃一个放羊老倌的头型,有时候还会咂两杯小酒,美滋滋的归去。

每逢春节或村里有客事,大爹就忙起来了。各家买了红纸只管送来,老先生会照单全收然后一丝不苟书撰写对联,分文不取还要提供茶水服务,而我作为贴身书童也乐得屁颠屁颠的,牵纸,磨墨,晾晒,感觉自己也是文化人了。大爹撰写的对联并不高妙,都是些“家住富饶金沙畔”之类的大白话,楹联格律范式也不严谨,但深得村民喜爱,通俗易懂,接地气;毛笔字也普通,尚达不到书法段位,但规矩隽秀,字如其人。
我到省城读书以后,和大爹见面的次数就少了,半年才可以放假回家一次,这给越老越念旧的大爹造成了很多牵挂。在此期间,我们保持了相对密集的书信往来,我可以随时知晓家中的情况,村里的消息,也可以夸张的向大爹炫耀外面的花花世界;尤其是那种带有毛体草书“XXXX大学”字样的牛皮纸信封不断往家中寄,特别能满足我的虚荣心,大爹也能从中获得极大的安慰愉悦,认为我非常成功。

有一种牵挂叫善意的欺骗。在我毕业但又没有正式找到工作的那两年,恰是大爹病势日趋严重、接近人生终点的两年。我们互相的通信风格基本是互相欺骗报喜不报忧,我因就业困难和打工的艰辛,家信汇报的基本是自己初涉社会不识愁滋味的豪情自信和决心,甚至把打工处私企老板给我们画的大饼也复制了附上;大爹的来信则是一如既往的关心牵挂,但对自己的病情一直是闪烁其辞或直接隐瞒不提,特别是正值壮年的大姐的遽然离世对他的巨大打击,在最后一封信中虽然不着一字却透出了几近崩溃的感觉,我似乎看到一个须发尽白强撑病体却假装精神饱满的倔强老头的身影。
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这是大爹晚年经常用来调侃自己的话,他一辈子热爱生活,珍爱生命,珍视亲情,同时也对即将终要面对的死亡持有近乎禅意的达观坦然。在给我寄出最后一封信后不久,一个晴朗的中午,他穿戴整洁,端坐在堂屋前的藤椅上,在家的族中晚辈都见过了,来串门的亲戚散坐院子里摆龙门阵,还有小孩子在嬉笑打闹;同辈中二大爹和姑妈去世得比较早,在城里工作的三大爹正在从下关赶回来的路上,现场只有我父亲和他,老哥俩慢悠悠的聊;大爹开玩笑的让家人给三大爹传话,赶路不要急,他自己实在撑不住就不等了,自己拔管子。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生告别会,气氛轻松幽默,有含泪的微笑,就像编剧出来的一样显得不真实。

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又是一年清明节,我带着孩子们陪堂哥和姐夫来到大爹坟前,他生前自己选定的坟地可以看到皮厂村全貌和部分他教过书的山寨村落,坟前是自家的葡萄地,他自己植下的圆柏已经十分高大挺拔了。压过了香纸和柳枝,我用当年他教我的刀法认真的割去了坟塚上的杂草,然后默默的读了两遍碑文所载的信息。没有忧伤,无需跪拜,我想,大爹是懂我的。
清平乐
三尺讲坛,鬓染层层霜。清贫甘苦不思量,身后桃李芬芳。
园丁蜡炬春蚕,植得贤才栋梁;百花成蜜过后,春泥护花依然。
2023年,清明
作者/赵思良
编辑/杨宏毅
审稿/吴洪彪
终审/杨凤云
投稿邮箱/bcrmtzx@163.com


网友评论文明上网,理性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