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川时讯•文化周刊】红土烽烟:云南抗战篇章(组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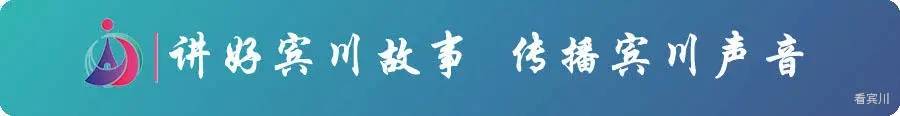


◎/刘志新
卢沟枪声响,日寇犯中华,“国之劲旅”滇军挺身而出,出滇抗日。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开始,地处西南边陲当时仅有1千万人口的云南,先后出兵42万(伤亡在10万人以上),组成第六十军、五十八军、新三军和老三军、九十三军等部队,冲出云岭大地,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浴血台儿庄,横扫湘鄂赣,血战中条山,坚守中越防线,参加滇西抗战,打出了抗日滇军的威风,写下了中国正面战场上最壮丽的华章之一。
——题记
 第一章:滇军出云
第一章:滇军出云
1937年
卢沟桥的炮火撕破残夜
日寇的铁蹄踏碎河山
“四万万人齐蹈厉”
而滇云深处
号角已震彻红土高原
“国之劲旅,四十二万!”
穿越金马碧鸡坊
冲出云岭雄关
彝家老爹塞来的普洱茶饼
压进行囊
火塘边捂热的银饰
此刻贴着冲锋的胸膛
苍山十九峰在破晓时列阵
洱海的波光淬成刺刀上的霜
六十军将士的绑腿里
裹着红河岸的土、茶马古道的尘
葫芦丝呜咽
吹裂了《小河淌水》的柔肠
“这不是调子,是出滇令!”
“子弟兵”三个字
被阿妹用绣花针烙在枪托
比大理石的纹路更深
比三迤大地的伤疤更烫
他们以彝文在弹匣刻咒
毕摩的经声在硝烟里回荡:
“此去不回,便做怒江的石头
让洪流把骸骨
冲成虎跳峡的浪!”

第二章:血浸惠通
1942年
畹盯失守,腾冲沦陷
日寇铁蹄长驱直入
滇西大地陷入腥风血雨
怒江把悬崖嚼成锯齿
惠通桥的钢索在炮火中绷紧
它记得,一个腾冲马帮的后人
用祖传的砍刀劈开第一道铁丝网
刀锋崩裂时,他咬碎牙齿吼道:
“这土地,一寸也不能让!”
高黎贡山的云海沸腾了
不是霞光,是燃烧弹泼红的天空
滚烫的弹壳砸进普洱茶田
焦土上横七竖八 那是
被炸断根的古茶树
像垂死的母亲,仍攥着一把带血的春芽
戴银镯的双手在硝烟里翻找弹药
那银镯,昨夜还绕着火塘跳舞
傣家竹楼拆尽千根梁木
每副担架都滴着新鲜的松脂——
“抬不动山河,就抬骸骨!”
而江对岸
日军用刺刀挑着婴孩的襁褓
笑声比枪声更尖利
六十军的机枪手突然沉默
他想起离家时
小妹塞进他口袋的那把松子……
“开火,开火!连同钢索嘶吼声
整条怒江跟着咆哮
浪头卷起带铁锈的漩涡
把日军坦克的残骸
冲成水葬的坟场!

第三章:松山祭
1944年,滇西大反攻
三十万发炮弹
将红土地翻耕成燃烧的祭坛
这不是播种,是涅槃!
焦土之下,青铜的根脉暴起
连成中国远征军的脊梁
爆破筒掀开的地壳里
火把节未跳完的舞步仍在旋转
彝人的铜鼓被弹片击穿
鼓声却卡在日军碉堡的射孔
闷响如雷……
“强度怒江!收复河山!”
三十万双草鞋踏碎激流
浪头啃噬着浮桥上的脚印
而对岸的悬崖
正被鲜血浇灌出新的石阶——
“这一仗,要让高黎贡山低头认路!”
龙陵的雨巷里
一封未寄出的信被战地记者拾起
钢笔字在雨水中蜿蜒
“阿妈,等山茶花开满山头,
我就回大理,给您砌座新火塘……”
墨迹与血渍在纸页上交锋
最终汇成另一条澜沧江
冲垮所有标着日文的战报
松山顶的月光,今夜格外锋利
它刺破硝烟,照亮战壕
身旁战友遗体摞成墙
像苍山十九峰忽然塌陷的一角
一个士兵用刺刀在岩壁上刻下:
“若魂归处无碑,这山河便是墓志铭!”
最后一笔落下时
东方的云层突然崩裂
一缕晨光如弹道般贯穿长空
正好击中
日军最后一个碉堡上那面破碎的旗

终章:山河铸魂
松山顶的月光仍悬在弹片上
照见:
西南联大上空飞机划破的晨雾
茶马古道马蹄铁迸出的星火
滇缅公路碎石里蛰伏的雷鸣
如今我指间摩挲的弹壳
内壁还嗡鸣着1944年的歌遥:
“三弦枕着弹壳调音,
山歌裹着火药飞……”
远征军墓碑的雨痕
那是横断山脉新长的骨节
当畹町桥界碑爬上青苔时
墓园钢哨突然自鸣并刺破寂静
高黎贡山挺直脊梁
抖落积雪
把凝固八十载的血泪汇成雪瀑
淬成千万把青铜利剑
悬在每一寸
受过伤害的天空
作者刘/志新
编辑/杨宏毅
图片来自网络
责编/杨宏毅
审稿/张进
终审/杨凤云
投稿邮箱/bcrmtzx@163.com


网友评论文明上网,理性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