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川时讯•文化周刊】给ga na一个好名字——干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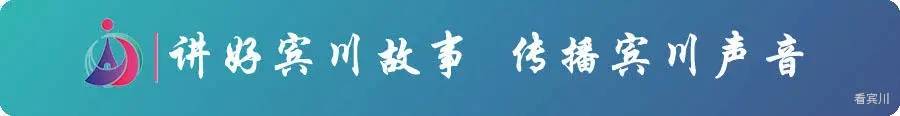


◎/杨志勇
白族有句俗话叫“红ga na,绿ga na,一年四季保平安”,这里面的“ga na”是一种用白族话语音来称呼的古老的传统食品,自古以来一直没有给它定下相应的规范化的汉字,虽然它早在古代就随着马帮向夷方各地传送,并在夷方落地生根,但它的名字也依然是口耳相传的被叫着“ga na”。在以前大理地区人走夷方的最重要的中转站滕冲古城,这种东西也依然被叫着“ga na”或者“gan lan”。

“ga na”是大理地区一种专门用来祭拜神灵的家家户户必备的米制品,我妈妈在世时,她每年就靠制作这种传统食品,在过年前的一两个集市,多少都还能挣下一小笔“巨款”!记得那时候,我二姐家女儿,我五哥家儿子都还很小,每年过年前的最后一个集市都会陪着我妈妈在牛井老四方街附近摆一个小摊去售卖。
 “ga na”是一种不知起源于什么时候,一直就与豆腐一起用油炸后成为拜神祭祖的必须品,它的生产工艺其实并不复杂,但特别考究。因为这是敬神的物品,在制作过程中都特别讲究洁净。首先要选用村里最好的米,打成米面,然后用最干净的水在最干净的面板上进行揉拌,揉好后再分成小团用特用的甑子或者新甑子蒸熟,然后趁热加上一些妈妈叫它为“姜黄”的纯植物染料给它染色,再继续揉制,直到加入的植物色素被揉均匀。这种“姜黄”一般只有三种颜色,就是红色、绿色和黄色,所以“ga na”制出来一般也就红、黄、绿三种颜色,整个大理地区用的都是这几种颜色。加了姜黄的面团要再次揉透,后揉拌成大块,用崭新的包袱包裹,外面再包上一层保温的东西,现在多数就是用崭新的保鲜膜来保温,制“ga na”要趁热进行再次加工,所以这个面块揉好时一定还要保持一定的温度,一般都是要擀制的取下来,其余的则还要保存在甑子里,擀完一块才取出另外一块。
“ga na”是一种不知起源于什么时候,一直就与豆腐一起用油炸后成为拜神祭祖的必须品,它的生产工艺其实并不复杂,但特别考究。因为这是敬神的物品,在制作过程中都特别讲究洁净。首先要选用村里最好的米,打成米面,然后用最干净的水在最干净的面板上进行揉拌,揉好后再分成小团用特用的甑子或者新甑子蒸熟,然后趁热加上一些妈妈叫它为“姜黄”的纯植物染料给它染色,再继续揉制,直到加入的植物色素被揉均匀。这种“姜黄”一般只有三种颜色,就是红色、绿色和黄色,所以“ga na”制出来一般也就红、黄、绿三种颜色,整个大理地区用的都是这几种颜色。加了姜黄的面团要再次揉透,后揉拌成大块,用崭新的包袱包裹,外面再包上一层保温的东西,现在多数就是用崭新的保鲜膜来保温,制“ga na”要趁热进行再次加工,所以这个面块揉好时一定还要保持一定的温度,一般都是要擀制的取下来,其余的则还要保存在甑子里,擀完一块才取出另外一块。
选一块专用的洗得特别干净的长条形的大理石石板,在面团上揪一小个面剂子,一般也就蚕豆大小,摆在大理石上,又用一根用了好几年,或许是几辈子,是由奶奶,甚至奶奶的奶奶传下来的小擀面杖,把那面剂子擀成一片细长的薄片。那就是“ga na”片,一般长20厘米左右,宽两三厘米,比纸还要薄上一些。擀出的“ga na”片被按顺序摆在一片篾芭上,摆满一篾芭就端到阳光下去嗮。
 在揪面剂子的时候,每揪一块都要把面团盖好,要防止它变冷,面团一变冷就擀不开,无法继续操作。擀好的“ga na”片很薄,每每都是擀面杖一擀通,就要用擀面杖借势把那薄片挑起来,如果你把擀面杖拿开,单独用手去取的话,很容易把那薄片弄坏,要再次揉成小团,再去擀一遍,如果冷了,更是要再次拿去回锅加热。
在揪面剂子的时候,每揪一块都要把面团盖好,要防止它变冷,面团一变冷就擀不开,无法继续操作。擀好的“ga na”片很薄,每每都是擀面杖一擀通,就要用擀面杖借势把那薄片挑起来,如果你把擀面杖拿开,单独用手去取的话,很容易把那薄片弄坏,要再次揉成小团,再去擀一遍,如果冷了,更是要再次拿去回锅加热。
 “ga na”嗮干,就要把它们收起来,红、黄、绿三色一样几片,一般二十片或者十片捆成一小捆,售卖的价格在以前是一毛、两毛一捆,后来是五毛,目前差不多要一两块,因为米的价格都涨到了两三块,人力成本更是到了一百多一个工。
“ga na”嗮干,就要把它们收起来,红、黄、绿三色一样几片,一般二十片或者十片捆成一小捆,售卖的价格在以前是一毛、两毛一捆,后来是五毛,目前差不多要一两块,因为米的价格都涨到了两三块,人力成本更是到了一百多一个工。
以前我的母亲擀这个“ga na”时,家里姊妹六个都不赞成,因为母亲那样子一坐就要大半天,甚至一整天,对母亲的腿脚的血液循环有很多不好的影响,可是妈妈却不愿意停下,因为那是她的妈妈,她的奶奶传给她的,她怎么会舍得放下呢!每次只要家里仅剩下她一个人时,她就会把偷偷准备好的一切拿出来,立马开干,一天要擀出好几篾芭来。做上一段时间,到过年前,就会做出好几大箱子来。
 每到过年过节,家里哥嫂、侄儿外甥女就都要帮她去销售。哥嫂在村里卖,我们村里制“ga na”的老人家很多,于是过年时排营街上卖这个的老人都差不多能摆几十个摊,所以家里只留一部分在村里卖。其余,则由妈妈带到城里姐姐后面在县城卖。那时,外甥女与侄儿都很小,哪年,在县城老四方街帮着卖“ga na”时,收到一张百元大钞,于是一老二小三个人居然没办法找补,最后还是让外甥女拿着钱跑回家里叫姐夫帮忙才给换成了零钱。因为那是家家户户过年拜神的必须品,我妈妈的工艺又特别好,比县城附近许多制作“ga na”的老人家做的都好,每年去县城售卖,都是早早就会被人们抢购干净。
每到过年过节,家里哥嫂、侄儿外甥女就都要帮她去销售。哥嫂在村里卖,我们村里制“ga na”的老人家很多,于是过年时排营街上卖这个的老人都差不多能摆几十个摊,所以家里只留一部分在村里卖。其余,则由妈妈带到城里姐姐后面在县城卖。那时,外甥女与侄儿都很小,哪年,在县城老四方街帮着卖“ga na”时,收到一张百元大钞,于是一老二小三个人居然没办法找补,最后还是让外甥女拿着钱跑回家里叫姐夫帮忙才给换成了零钱。因为那是家家户户过年拜神的必须品,我妈妈的工艺又特别好,比县城附近许多制作“ga na”的老人家做的都好,每年去县城售卖,都是早早就会被人们抢购干净。
 每年过年,家家户户把好吃好喝的东西准备好,都会单独用一个小锅,烧一点菜籽油,待油温合适就把“ga na”放到油里去炸。一只手捏着“ga na”的一角,一手拿着筷子,把“ga na”的另外一角放到油里去炸。因为油温够高,“ga na”够薄,二者一相接触,那“ga na”就迅速发泡卷曲。那时,另外一只拿筷子的手,就得迅速夹住发泡的部分,把它一点一点卷曲回来。放一点下去立刻就发泡一点,然后立马卷起来,说着是很慢,但整片放完进去其实也不过几秒钟时间,手脚要连环,刻不容缓,只要你慢一秒,那“ga na”片就卷不起来,会被炸成直直一片,甚至会被炸糊,颜色变成焦黑,味道也变得有些发苦。
每年过年,家家户户把好吃好喝的东西准备好,都会单独用一个小锅,烧一点菜籽油,待油温合适就把“ga na”放到油里去炸。一只手捏着“ga na”的一角,一手拿着筷子,把“ga na”的另外一角放到油里去炸。因为油温够高,“ga na”够薄,二者一相接触,那“ga na”就迅速发泡卷曲。那时,另外一只拿筷子的手,就得迅速夹住发泡的部分,把它一点一点卷曲回来。放一点下去立刻就发泡一点,然后立马卷起来,说着是很慢,但整片放完进去其实也不过几秒钟时间,手脚要连环,刻不容缓,只要你慢一秒,那“ga na”片就卷不起来,会被炸成直直一片,甚至会被炸糊,颜色变成焦黑,味道也变得有些发苦。

炸好的“ga na”片,卷曲成花朵一样,颜色绚丽,色彩斑斓,红的、绿的、黄的,几种颜色堆在盘中,摆在一起,一盘盘就像盛开的鲜花。看着那美丽的景象,我不由突然想到了它实际应该拥有的名字——干斓。“斓”字的古意为色彩驳杂、灿烂多彩,常用来形容花纹或色彩交错鲜明的样子。在古文中,“斓”多以“斑斓”“斓斑”等叠用或组合形式出现,如诗文中的“斓斑五彩服”,即用“斓斑”形容衣物色彩丰富。而这种古老的食品炸好的成品如果用一个字来作最贴切的描述,那一定就是“斓”。白族传统词汇里隐藏有许许多多的古汉语词汇 ,比如白族话里最常用的去上厕所的词汇“遗矢”,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里“廉颇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这两处用法,就是一模一样。
白族话说筷子叫“执箸”,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也是“先主方食,失匕箸”。其它这样的词汇还有很多很多,所以照这样看来这个“ga na”如果本来就叫干斓,就显得特别贴合,它同其它白族词汇一样,也是完全保留了古汉语的本意的词汇之一。
 现在有好多人记录这个食品,喜欢使用“干兰”这个词,其实“兰”的古义专指兰科植物,虽然在古代祭祀、礼仪中曾用“兰”(如兰草)来薰香、祭祀,如“兰汤”(用兰草煮的水,用于沐浴或祭祀),但与大理这个传统食品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的联系。传统食品“干斓”,用“斓”,表其色彩斑斓,而非“兰”,正是因为“兰”无“色彩”含义,仅有细微的一点点祭祀相关的关联;若写为“干蓝”,则会混淆“色彩驳杂”的本意,偏离食品因“红黄绿三色”而得名的核心特征。
现在有好多人记录这个食品,喜欢使用“干兰”这个词,其实“兰”的古义专指兰科植物,虽然在古代祭祀、礼仪中曾用“兰”(如兰草)来薰香、祭祀,如“兰汤”(用兰草煮的水,用于沐浴或祭祀),但与大理这个传统食品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的联系。传统食品“干斓”,用“斓”,表其色彩斑斓,而非“兰”,正是因为“兰”无“色彩”含义,仅有细微的一点点祭祀相关的关联;若写为“干蓝”,则会混淆“色彩驳杂”的本意,偏离食品因“红黄绿三色”而得名的核心特征。
在我过去完成的《云南小村排营小志》里,我就一直强调,“ga na”这个用白族话音色记录的古代食品就适合用“干斓”这个名字,但当时只是简单的表述了一下这个看法,没有从探讨研究的角度来肯定过这个名字的适合性和贴切度。

干斓一般在祭神之后,一撤下来就会被分食,它的味道甘香、酥脆。我们小时候,经济干枯,奶奶、妈妈去参加村里的一些传统活动,结束时会被分配到一些干斓、豆腐,她们都舍不得吃,总会带回来留给年幼的我们。那个时代,能吃到这喷香的干斓片,简直就是当时最幸福的事。
过去大理一带总会炸一些干斓,把它柔碎,再加上核桃末、芝麻、红糖、猪油等等配料制成元宵的“包芯”,也即馅料。用这种馅料包出的元宵,味道特别的香甜。所以那个年代吃到的元宵总是特别的叫人难以忘怀,到现在一不小心回味起来,总会不由自主的砸舌头,很想很想再次吃到那种美味,吃到那种妈妈的味道……
 如今,妈妈过世已经快三年,我们再也吃不到她亲手制作的干斓,那传了几代的擀面杖,大理石石板也渐渐蒙上了时光的薄尘,但每当过年闻到菜籽油的香气,看到集市上色彩斑斓的炸制米片,我总会想起妈妈坐在窗前揉面、擀片的身影,想起“干斓”里藏着的古汉语温度与白族人家的烟火传承。或许“干斓”这个名字,不只是对一种传统食品的精准注解,更是对妈妈那代人坚守的记忆留存——让这份裹着红黄绿三色、载着白族人民平安祈愿的味道,能顺着“干斓”二字,在往后的岁月里,继续与大理的风花雪月、过年的盛宴,一同被人记起、被人传承。
如今,妈妈过世已经快三年,我们再也吃不到她亲手制作的干斓,那传了几代的擀面杖,大理石石板也渐渐蒙上了时光的薄尘,但每当过年闻到菜籽油的香气,看到集市上色彩斑斓的炸制米片,我总会想起妈妈坐在窗前揉面、擀片的身影,想起“干斓”里藏着的古汉语温度与白族人家的烟火传承。或许“干斓”这个名字,不只是对一种传统食品的精准注解,更是对妈妈那代人坚守的记忆留存——让这份裹着红黄绿三色、载着白族人民平安祈愿的味道,能顺着“干斓”二字,在往后的岁月里,继续与大理的风花雪月、过年的盛宴,一同被人记起、被人传承。
图文/杨志勇
编辑/杨宏毅
责编/杨宏毅
审稿/张进
终审/杨凤云
投稿邮箱/bcrmtzx@163.com



网友评论文明上网,理性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