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川时讯•文化周刊】曾经的五里坡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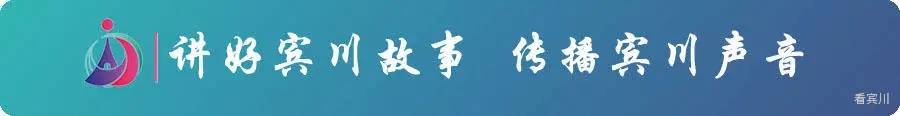


◎/杨树荣
从宾川县城出发,往鸡足山方向,在层峦叠嶂与田畴交错之间,一条被时光磨亮的古道蜿蜒向北。古道旁,花桥水库的碧波映着天光,而水库附近的花桥村旁,便是五里坡桥曾经矗立的地方。如今,20世纪80年代鸡足山公路改道的尘埃早已落定,这座曾经的交通要冲虽已废弃,却并未彻底消散在岁月里。残存的石桥墩和那棵老红柳树,仿佛还在与过往打招呼。杂草与灌木丛掩映下,溪水潺潺流淌,那声音仿佛带着穿透时光的力量,默默诉说着这座桥的岁月沧桑。
 五里坡桥,要从明代的风雨声里说起。它最初是一座精巧的木结构风雨桥,飞檐翘角,木梁交错,既能供人遮风挡雨,又能承载往来行旅的脚步,是鸡足山朝山古道上不可或缺的存在。明崇祯十一年(1638)农历腊月二十二日,徐霞客背着行囊,踏上了首次登鸡足山的旅程,五里坡桥便成了他此行中的一处印记。后来,他在《徐霞客游记》中细致记下了这段经历:“五里,有庵当岭,是为茶庵。又西北上一里半,路分为二:一由岭直西,为海东道,一循峡直北,为鸡山道。遂北循之。稍下三里而问饭,发筐中无有,盖为居停所留也。又北下一里,有溪自西南峡中出,其峡回合甚窅,盖鸡足南峡之山所泄余波也。有桥亭跨两崖间。越其西,又北上逾岭,一里,有哨兵守岭间。”文中那座“跨两崖间”的“桥亭”,正是五里坡桥。当年,徐霞客或许曾在桥亭下歇气,拂去肩头的寒气,望着桥下流淌的溪水,心中盘算着前方的路程,而这座桥,便这样悄然走进了历史的笔墨里。
五里坡桥,要从明代的风雨声里说起。它最初是一座精巧的木结构风雨桥,飞檐翘角,木梁交错,既能供人遮风挡雨,又能承载往来行旅的脚步,是鸡足山朝山古道上不可或缺的存在。明崇祯十一年(1638)农历腊月二十二日,徐霞客背着行囊,踏上了首次登鸡足山的旅程,五里坡桥便成了他此行中的一处印记。后来,他在《徐霞客游记》中细致记下了这段经历:“五里,有庵当岭,是为茶庵。又西北上一里半,路分为二:一由岭直西,为海东道,一循峡直北,为鸡山道。遂北循之。稍下三里而问饭,发筐中无有,盖为居停所留也。又北下一里,有溪自西南峡中出,其峡回合甚窅,盖鸡足南峡之山所泄余波也。有桥亭跨两崖间。越其西,又北上逾岭,一里,有哨兵守岭间。”文中那座“跨两崖间”的“桥亭”,正是五里坡桥。当年,徐霞客或许曾在桥亭下歇气,拂去肩头的寒气,望着桥下流淌的溪水,心中盘算着前方的路程,而这座桥,便这样悄然走进了历史的笔墨里。
 五里坡桥,是茶马古道上的一道重要坐标。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马帮是连接山间与外界的纽带,而五里坡桥,便是马帮必经的关口。马帮汉子们牵着马,驮着茶叶、布匹、盐巴,从这里出发,一路向西去往大理,再向北抵达丽江,将山里的物产运往外界,也将山外的新鲜事物带回山中。直到20世纪80年代,供销社所需的货物,依然要靠马帮或人力经五里坡桥运送。那时的桥,依旧是维系山里人生活的重要脉络,每一次马帮的铃铛响,都藏着人们对生活的期待。
五里坡桥,是茶马古道上的一道重要坐标。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马帮是连接山间与外界的纽带,而五里坡桥,便是马帮必经的关口。马帮汉子们牵着马,驮着茶叶、布匹、盐巴,从这里出发,一路向西去往大理,再向北抵达丽江,将山里的物产运往外界,也将山外的新鲜事物带回山中。直到20世纪80年代,供销社所需的货物,依然要靠马帮或人力经五里坡桥运送。那时的桥,依旧是维系山里人生活的重要脉络,每一次马帮的铃铛响,都藏着人们对生活的期待。
 对于家乡人而言,五里坡桥早已不只是一座桥,更是通往山外世界的希望之门。一代又一代的家乡人,背着梦想与生计,从这座桥上走过。我至今记得小时候跟着大人们去县城赶集的日子,天还没亮,村口就聚集了不少人,大家肩上扛着、背上背着自家从山中收割的茅竹和划好的竹篾,脚步匆匆却充满干劲,走到五里坡桥时,即使天色灰暗,偶尔会停下歇口气,桥下的溪水映着人影,桥上的木梁带着淡淡的木香,那情景成了我童年最深的记忆。大家带着山里的物产去县城售卖,再用赚来的钱买些油盐酱醋、针头线脑,或是给孩子添置一件新衣裳,而这座桥,见证了每一次出发的期待与归来的满足。
对于家乡人而言,五里坡桥早已不只是一座桥,更是通往山外世界的希望之门。一代又一代的家乡人,背着梦想与生计,从这座桥上走过。我至今记得小时候跟着大人们去县城赶集的日子,天还没亮,村口就聚集了不少人,大家肩上扛着、背上背着自家从山中收割的茅竹和划好的竹篾,脚步匆匆却充满干劲,走到五里坡桥时,即使天色灰暗,偶尔会停下歇口气,桥下的溪水映着人影,桥上的木梁带着淡淡的木香,那情景成了我童年最深的记忆。大家带着山里的物产去县城售卖,再用赚来的钱买些油盐酱醋、针头线脑,或是给孩子添置一件新衣裳,而这座桥,见证了每一次出发的期待与归来的满足。
 后来我到县城读高中,五里坡桥成了我求学路上最熟悉的伙伴。每次步行往返家校,我总会一次次踏上这座桥,每次走到桥心,都忍不住驻足片刻。那时的老红柳树已经长得枝繁叶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桥上,留下斑驳的光影;桥头的石板被往来的脚步磨得光滑,踩上去带着些许温润的触感;古老的桥木虽有些斑驳,却依旧稳固,仿佛在无声地鼓励着我。站在桥上,望着远处的山峦与近处的田野,心中总会升起一个个美好的梦想,梦想着考上好学校,梦想着去看看山外更广阔的世界,梦想着有一天能带着成就回到家乡。那些在桥上萌发的憧憬,如同桥下的溪水,在心中缓缓流淌,支撑着我走过一段又一段求学路。
后来我到县城读高中,五里坡桥成了我求学路上最熟悉的伙伴。每次步行往返家校,我总会一次次踏上这座桥,每次走到桥心,都忍不住驻足片刻。那时的老红柳树已经长得枝繁叶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桥上,留下斑驳的光影;桥头的石板被往来的脚步磨得光滑,踩上去带着些许温润的触感;古老的桥木虽有些斑驳,却依旧稳固,仿佛在无声地鼓励着我。站在桥上,望着远处的山峦与近处的田野,心中总会升起一个个美好的梦想,梦想着考上好学校,梦想着去看看山外更广阔的世界,梦想着有一天能带着成就回到家乡。那些在桥上萌发的憧憬,如同桥下的溪水,在心中缓缓流淌,支撑着我走过一段又一段求学路。
 时光流转,如今,交通条件早已今非昔比。宽敞平坦的旅游公路取代了昔日的古道,南来北往的汽车呼啸而过,将鸡足山的美景与宾川的物产更快地运往各地,方便了千千万万的人们。而五里坡桥的遗存,渐渐被繁茂的草木遮掩,知晓它故事的人也越来越少,或许再过些年月,它会被更多人淡忘。但在我心中,曾经的五里坡桥从未远去,它是徐霞客游记里的“桥亭”,是马帮铃铛声里的记忆,是家乡人赶集路上的陪伴,更是我青春岁月里的梦想驿站。那些刻在石桥墩上的岁月痕迹,那些藏在老红柳树里的时光故事,那些随着溪水流淌的温暖回忆,永远不会被抹去。
时光流转,如今,交通条件早已今非昔比。宽敞平坦的旅游公路取代了昔日的古道,南来北往的汽车呼啸而过,将鸡足山的美景与宾川的物产更快地运往各地,方便了千千万万的人们。而五里坡桥的遗存,渐渐被繁茂的草木遮掩,知晓它故事的人也越来越少,或许再过些年月,它会被更多人淡忘。但在我心中,曾经的五里坡桥从未远去,它是徐霞客游记里的“桥亭”,是马帮铃铛声里的记忆,是家乡人赶集路上的陪伴,更是我青春岁月里的梦想驿站。那些刻在石桥墩上的岁月痕迹,那些藏在老红柳树里的时光故事,那些随着溪水流淌的温暖回忆,永远不会被抹去。
作者/杨树荣
编辑/杨宏毅
责编/杨宏毅
审稿/张 进
终审/杨凤云
投稿邮箱/bcrmtzx@163.com


网友评论文明上网,理性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