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川时讯·文化周刊】漫步纳溪公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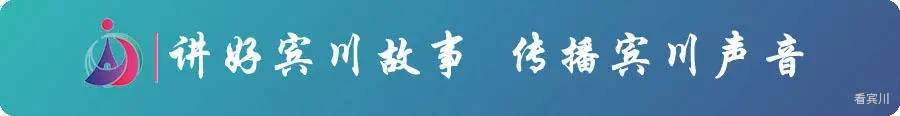


◎/唐红娟
已步入中年的我,身边许多圈子也随之渐行渐少。平时就正常的上下班,每到周末就是幸福的陪娃和遛娃,而纳溪公园慢慢的就成为了我精神栖息的港湾。
晨曦初微,我和爱人便陪女儿漫步到此。此时游人尚稀,鸟声却已织密了整个公园,一粒、一粒,从树梢间落下来。
殊不知,“啾啾”鸟鸣竟将一夜积存的清愁消解。
 园中树木极多,绿叶承载着朝露,晶莹圆润,竟如无数小世界,各自驮着一个穹苍,微风过处,露水便簌簌的跌下,钻入土中不见了。我想,这大约便是天地间的交接仪式,无人观礼而自有庄严。
园中树木极多,绿叶承载着朝露,晶莹圆润,竟如无数小世界,各自驮着一个穹苍,微风过处,露水便簌簌的跌下,钻入土中不见了。我想,这大约便是天地间的交接仪式,无人观礼而自有庄严。
公园西南一角,唢呐声像离弦的箭,穿透榕树下慵懒的蝉鸣。他笔挺挺的立于亭子的中央,古铜色的脸颊被岁月刻满沟壑,青筋凸起的手扶着锃亮的黄铜唢呐,十个指头在音孔上起落翻飞。每一次鼓腮换气,脖子就粗一圈,太阳穴旁的血管跟着搏动。唢呐碗口对着渐明的天空,像在向苍天发问。
那声音百转千回——时而裂帛般撕开晨霭,是黄土坡上信天游的倔强;时而又呜咽如诉,变成《百鸟朝凤》里那只失群的孤雁。几个老人停在不远处槐树下,有个拄拐杖的闭眼打着拍子,嘴唇无声地跟着翕动。
 曲调突然转为《江河水》,音符里仿佛看得见挣扎的腰鼓、飞扬的黄土、送亲队伍里突然决堤的眼泪。吹到悲切处,他整个身子微微颤抖,额角沁出细汗,仿佛把魂都灌进了这截枣木杆里。
曲调突然转为《江河水》,音符里仿佛看得见挣扎的腰鼓、飞扬的黄土、送亲队伍里突然决堤的眼泪。吹到悲切处,他整个身子微微颤抖,额角沁出细汗,仿佛把魂都灌进了这截枣木杆里。
随着一声轻叹我的思绪再次回归!男子精神焕发一曲《好汉歌》高亢嘹亮的旋律将《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们的不畏强权、顶天立地、重义轻利、肝胆相照、快意江湖的绿林好汉逐个播放。最后一个音在晨光中久久不散。他缓缓放下唢呐,露出磨得发白的唢呐杆上几道深痕。相继为他驻足的人默默散去,只有个穿校服的男孩还站在原地,眼睛亮晶晶的。这时我才看见,他脚边褪色的帆布包里露出半本《民间曲谱》,边角已被翻得起了毛。
 几位老者已在空地上操练起来,一人徐徐推手,似在抵拒无形巨物;一人单足而立,恍若临水照影的孤鹤;一人手执圆扇,随乐飘舞,宛若林中仙子般妩媚动人。她们的面庞上纵横的纹路,在晨光中竟显得柔和了许多,仿佛岁月刻下的不是伤痕,倒是智慧的印记。其中一位见我驻足,便微微一笑,也不言语,仍旧沉浸在他的太极世界中。我忽然觉得老人的晨练未必为了长生,或许只是与自己的身体达成一日最初的谅解。
几位老者已在空地上操练起来,一人徐徐推手,似在抵拒无形巨物;一人单足而立,恍若临水照影的孤鹤;一人手执圆扇,随乐飘舞,宛若林中仙子般妩媚动人。她们的面庞上纵横的纹路,在晨光中竟显得柔和了许多,仿佛岁月刻下的不是伤痕,倒是智慧的印记。其中一位见我驻足,便微微一笑,也不言语,仍旧沉浸在他的太极世界中。我忽然觉得老人的晨练未必为了长生,或许只是与自己的身体达成一日最初的谅解。
 林中的步道上准时出现了那个中年妇女,她牵着一条年迈的金毛,它的毛色在晨光里显得有些黯淡,步子缓慢而稳妥,带着一种经历过岁月的、不欲与人争辩的安详。金毛主人沿着步道慢跑而它也紧随其后一圈又一圈,直到他们的背影消失在葱郁的林中。
林中的步道上准时出现了那个中年妇女,她牵着一条年迈的金毛,它的毛色在晨光里显得有些黯淡,步子缓慢而稳妥,带着一种经历过岁月的、不欲与人争辩的安详。金毛主人沿着步道慢跑而它也紧随其后一圈又一圈,直到他们的背影消失在葱郁的林中。
 纳溪河畔新修的小湖边上小径那端,跑来了三三两两的青年,他们呼吸粗重,汗透衣裳。他们眼中有着老者所没有的焦灼,步伐急迫,像是在追逐什么,又像是被什么所追逐。科技时代的青年将自然囿于方寸屏幕之中,偶尔亲身来此,反倒显得局促了。
纳溪河畔新修的小湖边上小径那端,跑来了三三两两的青年,他们呼吸粗重,汗透衣裳。他们眼中有着老者所没有的焦灼,步伐急迫,像是在追逐什么,又像是被什么所追逐。科技时代的青年将自然囿于方寸屏幕之中,偶尔亲身来此,反倒显得局促了。
湖面平铺如镜,偶有两三小龟露出头来,却又快速的划开,湖面便漾开一圈圈的涟漪,将倒映的云影揉碎了又抚平,几个孩童蹲在湖边,专注的试图将小龟与自己的影子相连。他们的母亲,倚在围栏上,目光时而追随孩子,时而飘向远方,仿佛在思考今日的菜肴,又仿佛在回忆自己蹲在湖边的童年。
 我择了亭中一长椅坐下,看光影从叶隙间流过,在地面映出斑驳的花纹,忽觉公园之妙不在于景、而在于它容得下疾驰者,也容得下静坐者。既允老者追溯过往,也许少年展望未来,在这一隅之地,万物皆可按照自己的节奏呼吸。
我择了亭中一长椅坐下,看光影从叶隙间流过,在地面映出斑驳的花纹,忽觉公园之妙不在于景、而在于它容得下疾驰者,也容得下静坐者。既允老者追溯过往,也许少年展望未来,在这一隅之地,万物皆可按照自己的节奏呼吸。
从亭中起身,踏上小径,绕园一圈,忽觉纳溪公园迎来喧闹的一日,鸟鸣声也杂乱起来。
 但此刻的宁静已渗入每个人的心里,人们携着这一份宁静离去。纳溪公园算是完成了最初的使命——不仅仅作为风景被欣赏,更作为精神寄托的家园被体验。
但此刻的宁静已渗入每个人的心里,人们携着这一份宁静离去。纳溪公园算是完成了最初的使命——不仅仅作为风景被欣赏,更作为精神寄托的家园被体验。
作者/唐红娟
编辑配图/杨宏毅
责编/杨宏毅
审稿/张进
终审/杨凤云
投稿邮箱/bcrmtzx@163.com


网友评论文明上网,理性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