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客履痕】寻访法界圆净二庵遗址杂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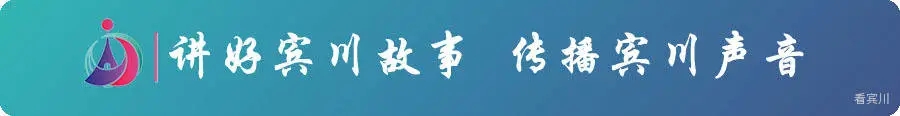


寻访法界圆净
霞客履痕:
寻访法界圆净二庵遗址杂记
袁蕊
追寻徐霞客的足迹,探寻鸡足山历史遗迹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历史以来,与鸡足山有关的史书少之又少,《徐霞客游记》便是记载较早,且最详实最丰富的史料,很多人游览鸡足山都会带上一本《徐霞客游记》,民国时期的高鹤年、费孝通等都是如此,他们都跟着徐霞客的记载去找寻相关的景观景点,并记下详细的游记。

寻访法界圆净
鸡足山历史记载的众多寺庵中,目前已恢复重建的有20座左右,其他大多都还湮没在深山密林中,冬春季节是钻入鸡足山深山密林探寻文化印痕的最佳季节,可以免去长虫的惊吓,也避免遇到突然恶劣天气及瘴气的侵害。鸡足山君师长期在景区工作,经常踏足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深山老林中寻找历史遗迹,是资深的鸡足山文化研究人员,探访遗址经验丰富,也知道圆净庵遗址的大体位置,于是便由君师带路,再次开始了寻访寺院遗址的行程,此次目的地是圆净庵及周边诸遗址。


寻访法界圆净
关于圆净庵的记载,史书上仅有只言片语,翻遍《徐霞客游记》,并未见到他对圆净庵的任何记载,是他当时并未见到这个庵院还是该部分手稿遗失?不得而知。毕竟他在山期间足迹可是遍布鸡足山的各个角落,多次攀崖穿林考察九重崖、罗汉壁、狮子林、旃擅林一带,独缺天池山下这一片的相关记载,鸡足山的游记和《鸡山志》书稿也有部分遗失。范承勋和高奣映的《鸡足山志》都有记载:“圆净庵(在白云居右岭),嘉靖间,僧周严建。”除此之外,在其他明清及民国的名家“鸡足山游记”中均未有圆净庵的游览记录。


寻访法界圆净
志书中,《大错指掌图记》详细记载了去圆净庵的线路:“(天池山)下为白云居,右为毗沙精舍,西即钵龙室,前为绿净山房。由南下坡。东转为断际处,从后西折为圆净,法界二庵。过倚杖溪、逍遥桥,为大乘、大士、大智、净觉、极乐、宝莲诸庵……”《鸡足山志》载:“钵龙室(在天池山下),天启间,僧琼明建。断际处(在五华庵上),僧寂定建。”根据志书上记载线路和大概位置,结合鸡足山全景图来看,圆净庵的位置大概在五华庵后半山腰偏西侧,从五华庵后门往西北可以直达目的地。然考虑到从石钟寺后往东行寺庵、静室遗址较多,或许能发现更多有价值的东西,而且沿着前人走过的古道会更有穿越历史的感觉,于是中午饭后,我们从石钟寺东面小路往北行走。大概一百米的路程后有一条岔道,左面是一片竹林,是前些年探寻过的大乘、大士、大智、极乐等庵遗址,右面是一条较深的沟壑,从北往南流向,目测有十多米宽,应该就是以前去往圆净庵的路。根据记载,这里应是倚杖溪,溪上有桥供人通行。据志书记载,这一代寺庵集中,水源丰富,大乘庵左侧有雨香泉,“或雨中生香,即斯龙之所致。”或许不是雨季的缘故,并未有雨香泉的痕迹,倚杖溪干涸已久,溪上的桥也不知被遗弃去了哪里,只有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石头被遗弃在溪涧中。还有书中的只言片语供我们去回味:“逍遥桥(在法界庵西,倚杖溪上),大错和尚修志片云居,担当老人隐居宝莲庵,无尽禅师宜断际处,恒与仙陀、眼藏诸衲子闲游至此,倚杖逍遥苍波,题桥为逍遥,溪为倚杖,志所怀也。”


寻访法界圆净
因河沟较宽,无逍遥桥可走,几人开玩笑说逍遥在心不在行,虽无桥我们也可学前人逍遥而过,即使我们文化和修为都与他们几位不在同一层次,但志同道合之人工作过程即是快乐之心旅。于是讨论着明代那些隐士立于桥头吟诗赋歌会面的场景,绕道沟壑稍浅处,下河底再拽藤而上,到对面山岭往东,从一段竹林中穿过,脚下已铺满鲜红色的落叶,红绿相间,满目冬季的萧条。半里后稍上坡便看见有大约两米宽的土路一直往东延伸,这便是连接各寺庵的古道,眼前不知曾经印下了多少人足迹的古道,大部分已被枯枝败叶覆盖,两边古树荫翳,落叶轻轻,述说着冬天的孤寂与岁月的无情。沿着古道走了一段路后,左边杂草灌木丛中隐隐有一条小路往东北折向,君师已先往前探路,立于高处告知我们要往小路上去,于是上坡,路越走越宽,一路依然除了树木荆棘杂草,并未见任何人烟气息,冬天的风被挡在了密林外,阳光偶尔会透过稀疏处斜射进来,感觉整个世界只有我们三个人的话语声和脚踩树叶的声音。


寻访法界圆净
经过上坡又下坡后,豁然开朗,一大片平地出现在我们眼前,平地前是大片竹林,君师说这应该是一个遗址,但不是圆净庵。于是我们顾不上休息片刻,激动地冲向那堆残砖断瓦,希望能翻找出有文字记载的东西。该遗址规模也还算大,分为上中下三阶,第二阶的平地是最宽敞的,这是典型的鸡足山寺庵建筑模式。经过一阵翻找,下面两块平地仅有少数散落的砖瓦,大部分的砖瓦、石头被人集中地堆放在第三阶,经过多年的遗址探访,我发现鸡足山的寺庵遗址被敲断的砖瓦都会集中堆放在一个地方,而不是在原地散落,不知是寺院破坏时有人有意为之还是后面去探寻的人的手笔。该遗址破坏也比较大,墙体只剩埋在土里的部分,大部分已被杂草树叶掩埋,如果不去翻找会很难发现,有一些泥土被翻过的新鲜痕迹,君师说这是野猪在附近寻食时拱过的印记。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我们不是臭皮匠,顶不上诸葛亮,但也在认真翻找后找到了一些古物。有两块相对完整的菊花图案瓦当,有大小不一的四大块断砖特别有意思,刻着在白云下飞奔的马匹,雕刻得栩栩如生,实在惊叹古人的手艺,妥妥的艺术品,是古代手艺人智慧的结晶,但七拼八凑都是各成各形,不能拼出一块完整的砖。另外云纹还有简单线条的各类筒瓦、砖块都和其他遗址的差不多,碎了一地。先是有一块断碑被反扑在堆放的砖瓦中,经过清理后,碑上的字逐渐清晰地展现在眼前。该碑是块墓塔碑,长方形普通大理石材质,仅剩上半部分,中间是“清圆寂具戒比……”字样,右侧刻有年代:“大清嘉庆十……”。第一块有字碑的发现让我们有了继续翻找的信心,接着便发现第二块第三块,其中一块相对完整,也为长方形大理石,碑头刻有“诸法无常”4字,右侧是年代:“同治六年孟夏月吉旦”,中间是“清圆寂具戒比丘上湛下棱讳恩师传墓”,左边为落款:“孝徒寂祥寂吕、孝孙淳增”。还有一块仅剩圆形碑头部分,只能看到“永历五年冬月”字样,几块残碑字体都为颜楷,书法刻法水平一般,许是寺院僧尼自己印刻。遗址上古树已长成各种奇形怪状的样子,经过岁月冲洗后的石头纹路也相当奇特。往西有一块稍陡的空地,处于相对低凹的位置,地方不大,堆着一些相对规整的石头,看样子是个静室遗址,并有一条浅壑从旁边经过。虽然没有界碑作为证明,但翻阅相关记载和遗址所处的位置来看,这里大概率就是法界庵遗址。

寻访法界圆净
《鸡足山志》载:“法界庵,(在圆净庵右岭),万历初间,僧圆心建。康熙壬寅,僧广息重修。”“青鸟泉,法界庵有溪过无我庵,泉当其际。有青鸟啄树果于是溪,似醉,则饮泉水以醒焉。”在其“附诸庵院静室(凡五十二所)”部分又载:“柔绿轩(在法界庵左),崇祯十年,僧无为建。”“处约室(在法界庵右),崇祯四年,玄要建。”文字可以还原出历史的原样,明清时期法界庵的样貌此刻已清晰地出现在眼前,法界庵坐北向南立于中间,飞檐翘角、幽静清丽、香烟袅绕、钟鼓相磬,两边有静室,有僧尼修行,一条小溪从左边静室流过,小鸟鸣啼,在溪边轻轻啜水。此时此刻,感觉自己已如徐霞客在玉龙瀑布时一样,“此身非复人间”。直到黄老提醒我要继续前行,才猛然醒来。


寻访法界圆净
前半段路程处于寻找的状态,也绕了一些弯路,耽搁了较长时间,接下来的路要稍微轻松些,既然已找到法界庵,那圆净庵就不远了。想到今天马上就要到到达目的地了,激动的心便无法掩饰,脚步不觉加快起来。过静室遗址后稍上坡,就已看见对面另一边山岭有大片绿茵茵的竹林,老干新枝相间,竹叶轻轻晃动,像是在用特有的方式迎接多年不见的友人。大概十多米长、半人高的石墙映入眼帘,君师告知已到今天的最后一站——圆净庵。从法界庵到圆净庵相邻,仅需3分钟的路程,却被中间一条沟壑分在不同的两座山岭。黄老师既是明师,也是做事很细心周到的前辈,走在前面找最容易上坡又安全的道路,拉开倒地的树枝和拦路的荆棘,以便我们顺利前行,避免挂坏衣服或者树枝反弹会拍打到后面的人。我们跟随黄老的脚步顺斜坡从几棵竹枝中间穿过,两边的竹枝还是会时不时牵动着我们的衣角,忽然想起李白的“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石墙边的那段路有些滑,上去的时候还是需紧紧拽扯住旁边的树枝。越过石墙,便看见一块界碑孤零零地立在几米外竹林间,“圆净庵,宾川县人民政府一九九八年二月立。”与众多遗址界定碑一样,都是由熟悉鸡足山寺院的沙址当地老人和相关部门、鸡足山文化研究者共同界定立碑。黄老立于碑前静思,我知道他的诗此时已成形于脑海,许是在回忆圆净庵的历史,或在感伤曾经的历史沧桑,或是在重绘庵院的样子。放眼望去,遗址与其他地方都差不多,满目疮痍,落木萧萧,而从那四五处断墙遗迹来看,圆净庵的样子更容易想象些,从其遗址的范围及几截断墙来估算,圆净庵也是鸡足山庵院中规模比较大的了。高奣映的《鸡足山志》“附诸庵院静室(凡五十二所)”记载:“翠柏居(在圆净庵),天启元年,僧洪时建。华池室(在圆净庵右),崇祯十五年,僧三池建。”虽文字较少,但从落入眼帘的实景可以大概绘制出圆净庵曾经的模样。圆净庵的建筑模式和法界庵的差不多,坐北向南,大殿后是一大片翠竹林,殿前松柏参天,庵院两边为静室,翠柏居的位置要朝后一些。圆净庵遗址最大的特色是竹林,整片竹子将遗址包围在中间,让原本荒凉孤寂的地方多了些生机,想来在四面种上竹子的那个人也是风雅之人,这里也许是许多隐士向往的清修之地,毕竟谁不喜欢“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潇洒人生。




圆净庵这块区域看起来湿度比其他地方要大,那些陈年砖头上已铺了厚厚的苔藓,树林更加茂密,气温也感觉低了一些。在遗址上,我们依然翻找着,却发现与其他地方无异,大部分是普遍的菊花、荷花、云纹等残砖断瓦,有一块瓦的花纹有些独特,像是太阳,在其他遗址还没见过。整块地方相对完整的还是翠柏居,四面半人高的断墙还坚固地立在那里,把那块十多平米大的空地围在中间,几棵古柏树立于墙外,墙头都是岁月斑驳的痕迹,空地上还堆放着一些砖块和杂物,前些年也许曾有人在这里搭棚住过。南面断墙中段有一个用瓦搭建的拱形建筑露出地面,刚开始我们还以为是灶台或者壁炉、佛龛之类,君师用手扒开旁边的杂草枯枝后,发现里面并没有用火的痕迹,因此否定了这种想法。经过黄老四面勘测,再结合其所处的位置,最终认为应该是门头,最上方由泥土覆盖,中间用瓦片做成拱形,两边用砖块砌成门框,与上世纪那些门头建筑一般无二。圆净庵的考察已划上句号,黄老的《寻圆净庵遗址》诗也吟响在青山绿水间:
林深苔滑庵何处?
越涧攀崖道隐藏。
忽见青青丛竹外,
断墙无语对斜阳。


用了半天的时间,今天考察遗址的行程终于圆满结束,从倚仗溪到圆净庵,一路有坎坷,有平坦,只见“千岩奇秀”,未见“万壑争流”。在多次寻访遗址后,越来越发现知识的匮乏,大学仅学到那点考古学知识也已随时间消磨全部还给了老师。在这岁月静好的时光,鸡足山深山密林间,那些辉煌已逝去,却留下那些残垣断壁、古树藤蔓向世人述说着鸡足山千百年的风雨历史,供后人不断去翻阅、倾听。






寻访法界圆净
图文/袁 蕊
编辑/杨宏毅
责编/李 蓉
审稿/安建雄
终审/杨凤云 张进

网友评论文明上网,理性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