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川时讯•文化周刊】过 年(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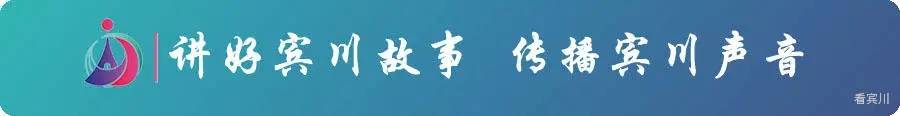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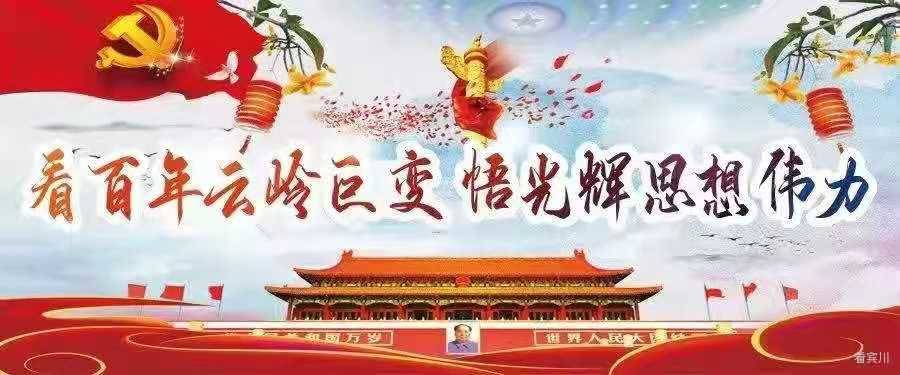


·赵思良
扶贫下乡的时候,在一个偏远的山村农家小院,简陋的柴门上,见到一副不俗的春联“回家过年犹多味,依俗庆春乐无穷”。行草诙谐俏皮,小院意趣盎然。飘着炊烟和腊肉香味的,是几近衰朽的土木老屋,旁边是刚建了一层半就停了下来的砖混洋楼,暖色的青砖和刺空的钢筋,暴露了主人外出农民工的身份。

勤劳朴实,热爱生活。相较于邻近县区的粗犷随性,这里的村民多了一点精打细算和俭约务实。每年过年回家,带回来的除了难得的天伦孝爱和亲友往来寒暄,还有这一年中在外务工省吃俭用积蓄的三五万硬货,置办年货及生活日常支出之余,就是把祖传的住房进行现代化改造,以示一代更比一代强。一般的操作程序是,借每年回家过年的一个月时间,在老地基上钢筋水泥砂石砖头的干上一圈。积蓄花完的时候,年也过完了,于是收拾行装约上同村的工友再上路,继续新一年的务工周期,期待着明年过年回来再浇筑上一圈。明年无疑是值得期待的一年。一年复一年,一圈又一圈,如此这般经过五六个周期轮回,小洋房盖出水大功告成,一个勤劳致富的标本便制成了。

当出门在外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方式,过年成了回家的唯一机会和理由。回家过年不仅仅是为了盖房子,是这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的一种信仰,一份责任,是一个民族灵魂的召唤。不是我吹牛,每年春节,全国数以亿计游子的归心,足以挤爆地球上最完善、最先进、最大规模的交通运输系统。春运期间,多少人以不同的方式上演着人在囧途的故事:战斗英雄一样的排队抢票,弱智呆傻一样的被票贩子敲诈勒索,干板菜一样被晾在堵死的高速公路上,土豪财主一样的包车买路,流浪乞丐一样的抛锚凌乱在荒郊野外刺骨的寒风中吃冷水泡面。像南归的雁群,像回溯的马鲛鱼,千难万险阻止不了行者的脚步。同一趟囧途,同一个梦想:回家过年。

我关于过年的清晰记忆,始自1984年春节的那次失败的年货投资。金沙江南岸的皮厂村,地不逾里,人不满千。春节前的最后一个街天(尽头街),达到了一年中人流物流的最高峰。四山头的原住村民,平川街来的摊贩,牛井来的城里人,把巴掌大的一块斜坡集市挤得几近燃点。
潦潦草草吃过早饭,我翻出了一年来的所有积蓄,再次认真的数了3遍,没错,就是8角4分钱。小心翼翼的揣着钱,我挤到了卖炮仗的摊位前。面对那些朝思暮想花花绿绿的炮仗,准备做人生最大的一笔交易。天桥牌电光火炮,包装紧实,响声清脆,哑炮少,是投资首选。炮仗整卖8角5分钱一封,有100头;也可以拆散了零卖,1分钱1头。虽然还没有上过学,但我很清楚我的资金链有问题。纠结,犹豫,自己跟自己整整内斗了两个钟头,我到底没能抵制住诱惑,终于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出手了:把满是汗渍的8角4分钱硬币阔气的排在了摊贩的案板上,如获至宝的捧着摊主帮我数了两遍的84头炮仗飞回家,关上房门再认真的数了N+遍。爹一直在忙着宰鸡、烧洗腊猪头,并没有察觉到我的异常,却似乎看透了我的内心,问我买炮仗的钱够不够,不够的他给添上,凑足8角5分钱就可以买足100头的一封了。我马上要晕倒,却含泪强作镇定:不消了,我的钱够呢。

花钱买炮仗,乐得一声响。大年初一早上,我在半个小时内快速的放完了84个炮仗,然后尬尬的看着别的小朋友开心放炮的时候,终于冷静下来明白了一个真理:冲动是魔鬼。1分钱的低级失误,16头天桥牌电光炮仗的巨大损失,让我懊恼自责了30多年,至今无法释怀。此后,我便落下了一个抠门小气的毛病:连捡到的瞎炮仗都舍不得放完,小心的用纸盒装好藏在楼上的墙洞里,第二年再翻出来放几个,又把新积攒的瞎炮收藏好,年年有结余,直至前年拆老屋才把它们全销毁了。

除了玩炮仗,过年还有更多的幸福主题。大概在一个星期前,过年的各项活动就条理有序的开展了。村里的打浆机磨面机日程紧张,磨豆腐和打饵块(年糕)需要提前排队预约;有时会有外县来的游脚手艺人,扛着爆米花机走村串巷流动设摊作业,村民自带玉米或大米和干柴,每炮收两角钱的加工费,新出锅的爆米花清香扑鼻,用糖稀裹成团,可以哄住所有哭闹的小孩。

大人们的年货,小孩不感兴趣。主要是买年画、灶神、香纸、老黄历、水果糖、茶叶,等等,买来红纸请教书的大爹写春联。全家人的被窝需要在年底全面浆洗,母亲用一整天的时间搞定,确保新年第一夜可以盖上散发着肥皂香味的被窝;大年三十,全家总动员,大扫除,把一年来无暇顾及的里里外外旮旮角角全部抹洗得一尘不染,然后就可以准备年夜饭了。

年猪是一个月前就杀好了的,此时已经腊味飘香了,那是全家人一整年的肉食。只有猪头肉和自家养的鸡才是年夜饭的当家主角,偶有鱼肉、牛羊肉加持,配上各种汤炒素食,满满一大桌,大人们倒上自酿的小甑酒,给孩子们倒上汽水,那简直是太完美了!其实,刚刚挨家逐户全村轮吃过了整整一个月的杀猪饭,此时面对满桌的美味佳肴,大家都少了平时那种野狼恶虎般的战力,斯斯文文热热闹闹的吃完饭,便在火塘边坐待零点的爆竹炸响。

1997年以前的皮厂村,不通电,大年夜没有春晚可看,只有通宵的爆竹声响,把全村的狗吓得集体躲进后山,两天后才敢夹着尾巴怯怯的回家。熬年夜,几个串门的亲戚点着马灯围着火塘摆龙门阵烤茶吃,我们兄妹则围着母亲的灶台,滴拉着口水看她熬麦芽糖。用红薯或包谷熬煮汁水,用麦芽水点卤,在大锅土灶上熬煮一个通宵,才形成糖稀。核桃吃不起,就事先炒好一簸箕花生仁,晾冷后搓揉掉红皮备用。待天色微亮,全家人都困得挂起两个大熊猫眼圈的时候,糖稀出锅,再把花生仁均匀的搅拌进去,冷却硬化,美味即成。

初一不出远门。枯水季节,金沙江两岸靠水边裸露出大片的沙滩,阳光下在巨大的礁石间一闪一闪的泛着金光,这是皮厂人的旅游胜地。这一天,全村的皮娃娃都到大沙坪集中。在柔软干净的沙地上摔跤翻跟斗,往江水中扔炮仗,在死水塘里摸虾,围成圈拉着互不通语言的傈僳族少年的手跳踢脚舞,累了饿了就着江水吃自带的红薯干、炒花生和麦芽糖。

初二开始,年内有新娶的青年要和新媳妇回娘家拜年,而有新嫁女的人家则准备迎接外嫁闺女回门。以此为由头,村内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挨家逐户轮庄请吃和吃请年饭,直至正月十五才算真正把年过完。

30多年间,村里过年的习俗在保留了基本框架的前提下,也在慢慢的变化。经济条件的改善和兴趣爱好的转移,炮仗的数量一度达到历史峰值便迅速回落,近年只有仪式性的几声响,年夜饭开席时放一封,新年零时准点放一封,初一早上起床再放一封,稀稀拉拉的此起彼落。新成长起来的小娃娃们也再不会为几个小花炮废寝忘食,他们现在玩的是礼花,焰火,高端大气。我有心理阴影,虽然不好意思再玩炮仗,但每年都会报复性的买一大堆,鼓励孩子玩个够。

年夜饭的主角没变,但已不追求数量和荤菜比例,有特色,健康爽口即可。小屏幕直播的春节晚会,迅速的被吹捧又迅速的被冷落,最终被娃娃们的动画片取代;年轻人则争分夺秒的集结,一圈一圈的通宵斗麻将。有了点过年的小钱,都有点飘。现在农村也不准玩麻将了,是该开发新的替代项目了。
应该为老爷子们的项目点个赞。村里成立了老年协会,主要活动项目是吹拉弹唱,七长八短的土洋乐器配上老腔土调,把洪湖水浪打浪之类的老歌演绎得别有一番韵味。老头子乐队平时每星期定期开班,大年三十晚上达到高潮,应该算是我们村的春节晚会吧。晚会演出比较成功的节目会继续操练打磨,准备初三到观音寺参加整个平川地区的文艺汇演。


金沙江皮厂段下游十公里处建起了鲁地拉电站,水位大涨且常年平稳,大沙坪被淹没了,电站大坝以上数百公里枯瘦的大山峡谷间,出现了一道亮丽的风景。高峡出平湖。壁立千仞,傲骨与清波齐美;镜开万顷,江水共长天一色。大自然的洪荒之力加上人类工程的如虹气势,给小小的皮厂村引来了无数观光游客。好风景都在险峻处。春节期间,峭壁上凿出来的沿江公路边上,停满了外地车。此情此景,皮厂人焉能旁观?

我因为自己的原因,毕业后没能及时就业,在外漂了整整三年,家不成业不就,混得很是难瞧。其间有一年春节没有回家过年,因为怕让家人难过,怕被长辈问及领多少工资,怕被亲戚介绍对象甚至催婚逼嫁,所以我选择了逃避,留在城里过年。那么大的一个城市,大年三十人突然走完了,空荡荡的成了一座鬼城,街上冷冷清清一个人也没有,想吃一碗炒饭也找不着开门营业的店家。过大年吃泡面,出租房里看彩电。这个春节留给我的记忆,讽刺意味一点不弱于1984年的那几个炮仗。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春节期间会有那么多的归雁和马鲛鱼,因为城里有乡下人的梦想,乡下有城里人的故乡。过年,让所有的城里人和乡下人原形毕露。


清红路两侧的路灯竿上,城管的工作人员在挂大红灯笼。年味越来越浓,忽然有些想家了,灵魂深处那急不可耐的归心再次被街上的声声爆竹唤醒:
迎新爆竹辞旧钟,
新桃旧符样样红。
回家过年犹多味,
依俗庆春乐无穷。
作者/赵思良
编辑/杨宏毅
审稿/吴洪彪
终审/杨凤云
投稿邮箱/bcrmtzx@163.com


网友评论文明上网,理性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