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川时讯•文化周刊】红糖米花开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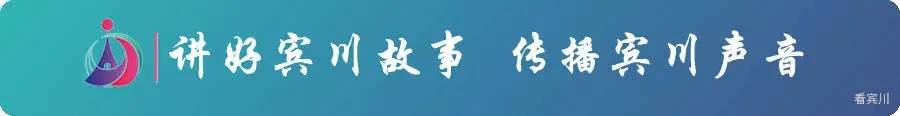


•蛮 子•
在大理的宾川,有一种春节美食叫米花。说来自豪却也搞笑,到高中毕业我一直以为米花是全中国人春节的节日食物之一,和北方面食南方米饭一样正常。之后到省城读书,才知道米花原来是地方特色的家乡食物。这个不大不小的发现让我惊异又欢喜,在我的认知里,米花从此就闪耀着乡愁的滋味,洋溢着乡土的芬芳,飘荡着节日的欢天喜地,而且会在家乡餐桌上代代相传。
 宾川米花的传统制作简单、美好,像个吉祥的乡愁故事。腊月初始,各家各户就会开始精选颗粒保持较好的糯米以制作“阴米”,这是米花制作的主要食材。然后是淘洗,接着是在甄子里蒸熟,这个火候考究,不能蒸太过。蒸熟后倒在簸箕里阴干。阴干的过程中需要将糯米饭团多次揉散,不能用力过猛,以尽量保持米粒的完整不断。待阴干后,“阴米”制作即告完成,这个过程要十多天。
宾川米花的传统制作简单、美好,像个吉祥的乡愁故事。腊月初始,各家各户就会开始精选颗粒保持较好的糯米以制作“阴米”,这是米花制作的主要食材。然后是淘洗,接着是在甄子里蒸熟,这个火候考究,不能蒸太过。蒸熟后倒在簸箕里阴干。阴干的过程中需要将糯米饭团多次揉散,不能用力过猛,以尽量保持米粒的完整不断。待阴干后,“阴米”制作即告完成,这个过程要十多天。
值得一提的是新蒸糯米出甄之时,蒸汽缭绕,糯米饭清香扑鼻,此时奶奶或是母亲大多就会盛一碗热腾腾喷香糯米饭,舀一勺切碎的红糖拌上,递给早已馋涎三尺的孩子。人世间最隆重的春节就这样从孩子们那一碗拌着红糖的糯米饭开始。那一刻的美好记忆是每个孩子一生萦绕在心底的温暖,是春节记忆中最温热的部分,那缭绕着糯米饭香的一碗是满溢的温情传递,从此你永远挂怀着人世的情意。心底只有软糯的温饱,不复在意冬天里的艰难。
阴米制作完成了,还不算,家乡人总要舀出一碗半碗阴米来染红再晾干,然后又混回阴米里。待春节前三、五天家家户户便开始聚集在每个村能炒制米花的人家,排队炒米花。那时节寒冷正甚但也冻不住乡间迎春的热切,炒米花的炉灶里红堂堂的火焰硬生生逼退了冬寒。
 我奶奶能炒一手好米花。每年的春节前十来天,我家院内就会架起大锅,生上煤火,奶奶拿出藏储在陶罐中炒米花用的细砂,那砂经过一年一年的使用,被香油和温度历练成黑色。奶奶炒米花的手艺在村里被人称道。那火候的拿捏,砂中香油的量,炒拌的节奏,起锅的时机与炒制的娴熟,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每年我都从奶奶的心情里看到奶奶对自己手艺的骄傲。而奶奶整天整天炒米花的劳碌和那时生活的艰辛,也深深埋藏在了我年少的心底。
我奶奶能炒一手好米花。每年的春节前十来天,我家院内就会架起大锅,生上煤火,奶奶拿出藏储在陶罐中炒米花用的细砂,那砂经过一年一年的使用,被香油和温度历练成黑色。奶奶炒米花的手艺在村里被人称道。那火候的拿捏,砂中香油的量,炒拌的节奏,起锅的时机与炒制的娴熟,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每年我都从奶奶的心情里看到奶奶对自己手艺的骄傲。而奶奶整天整天炒米花的劳碌和那时生活的艰辛,也深深埋藏在了我年少的心底。
 于是从米花炒制完成,村人似乎每家便都有了待客的底气。大理宾川的习俗是,每年年前结婚的和其他的三亲四友便会在正月里前往亲戚家拜年、访亲。客人一到,主人家便用烧好的开水为客人奉上一碗红糖米花,在热气和香味的缭绕中,情份便随着交谈渐渐地浓了起来。随后才开始杀鸡煮肉地展开主食制作,这样的待客之道无疑让人心里甘甜。崇祯十一年(1638)腊月二十八日,大旅行家徐霞客在宾川鸡足山对这一碗红糖米花开水的款待亦感而记之,曰:“僧瀹米花为献,甚润枯肠”。这一碗红糖米花弥漫的温暖早已穿越了数百年。
于是从米花炒制完成,村人似乎每家便都有了待客的底气。大理宾川的习俗是,每年年前结婚的和其他的三亲四友便会在正月里前往亲戚家拜年、访亲。客人一到,主人家便用烧好的开水为客人奉上一碗红糖米花,在热气和香味的缭绕中,情份便随着交谈渐渐地浓了起来。随后才开始杀鸡煮肉地展开主食制作,这样的待客之道无疑让人心里甘甜。崇祯十一年(1638)腊月二十八日,大旅行家徐霞客在宾川鸡足山对这一碗红糖米花开水的款待亦感而记之,曰:“僧瀹米花为献,甚润枯肠”。这一碗红糖米花弥漫的温暖早已穿越了数百年。
 不过,如果单单就那么一碗红糖米花开水,虽然庄重深情,却未免单调,于是以米花就锅下菜,米花糖像童话一般生发出来,圆球形的红白相间,方块的、条形的或红或白,点缀着或花生米、或核桃、或爆玉米花、或芝麻……春天还在地下蓄势,孩子们的米花糖却在喷香的厨房弥漫开来。生出那一碗温暖的米花开水,更生出民间无限的烂漫来。
不过,如果单单就那么一碗红糖米花开水,虽然庄重深情,却未免单调,于是以米花就锅下菜,米花糖像童话一般生发出来,圆球形的红白相间,方块的、条形的或红或白,点缀着或花生米、或核桃、或爆玉米花、或芝麻……春天还在地下蓄势,孩子们的米花糖却在喷香的厨房弥漫开来。生出那一碗温暖的米花开水,更生出民间无限的烂漫来。
 现在奶奶已过世多年,但每年春节,每当我捧吃起那一碗年味的米花,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就想起奶奶来,想起奶奶操劳的人生,感佩于奶奶那份对人生的勤劳与热爱,生生不息,奶奶没有说出来,但她做到了。就像温润我们肠胃的那碗米花,经过辛苦工序的成长,沸腾的开水,甜甜的红糖,充满温情的核桃末,那画龙点睛般点缀在整碗米花开水中的红色米花,人间的所有温情、烂漫和传承都齐备了,充满生机和希望。一方水土一方口味,食无定势,正如诗词文章,千篇一律那必然味同嚼蜡。重要的是五分厨艺更兼五分心意,非如此饭菜必无灵魂,“食人间烟火”说的就是一饭一食之间,那无限温情的人间眷念,“食色,性也。”也在其间。正如这一碗红糖米花,是我的底气,也是宾川人骄傲的人间。
现在奶奶已过世多年,但每年春节,每当我捧吃起那一碗年味的米花,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就想起奶奶来,想起奶奶操劳的人生,感佩于奶奶那份对人生的勤劳与热爱,生生不息,奶奶没有说出来,但她做到了。就像温润我们肠胃的那碗米花,经过辛苦工序的成长,沸腾的开水,甜甜的红糖,充满温情的核桃末,那画龙点睛般点缀在整碗米花开水中的红色米花,人间的所有温情、烂漫和传承都齐备了,充满生机和希望。一方水土一方口味,食无定势,正如诗词文章,千篇一律那必然味同嚼蜡。重要的是五分厨艺更兼五分心意,非如此饭菜必无灵魂,“食人间烟火”说的就是一饭一食之间,那无限温情的人间眷念,“食色,性也。”也在其间。正如这一碗红糖米花,是我的底气,也是宾川人骄傲的人间。
 今天,炒米花需要的糯米已经不再是旧时那样的稀罕珍贵,在平常的日子无非是家和超市的那点距离。但每年的正月初一清晨,宾川人依旧会把那三碗红糖米花开水,恭恭敬敬地供奉在祭祖的供桌上,天地祖先各自领享。唯一的变化是每碗米花上的筷子从一支变成了一双,现在又从筷子变成了小瓷勺,社会进步的富裕祖先也理应祭享。
今天,炒米花需要的糯米已经不再是旧时那样的稀罕珍贵,在平常的日子无非是家和超市的那点距离。但每年的正月初一清晨,宾川人依旧会把那三碗红糖米花开水,恭恭敬敬地供奉在祭祖的供桌上,天地祖先各自领享。唯一的变化是每碗米花上的筷子从一支变成了一双,现在又从筷子变成了小瓷勺,社会进步的富裕祖先也理应祭享。
 如此,第一道春祭,红糖米花开水,庄重,不泛热爱。和所有天下的美食一样,地方普众在舌尖味蕾的个性分明,传达并演绎着地方山水和人文传承的全部基因密码。这需要我们“吃”之以恒地去饱尝和经历。而这碗红糖米花开水的背后蕴藏着宾川民间的全部温暖与对生活的无限情意。
如此,第一道春祭,红糖米花开水,庄重,不泛热爱。和所有天下的美食一样,地方普众在舌尖味蕾的个性分明,传达并演绎着地方山水和人文传承的全部基因密码。这需要我们“吃”之以恒地去饱尝和经历。而这碗红糖米花开水的背后蕴藏着宾川民间的全部温暖与对生活的无限情意。
作者/蛮 子
编辑/杨宏毅
责编/杨宏毅
审稿/张 进
终审/杨凤云
投稿邮箱/bcrmtzx@163.com


网友评论文明上网,理性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