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川时讯·文化周刊】光阴细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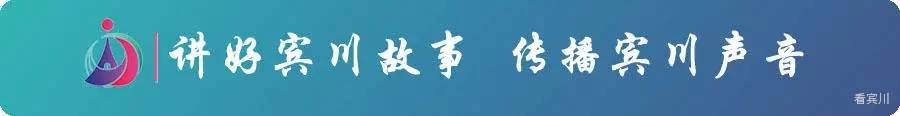


◎/李红文
这十年的光阴,说来也长,想起来却只是一转眼的工夫。我同宾川高平一中,竟也相伴了十年了。十年前,宾川一中的搬迁搞得沸沸扬扬。后来便亲历她的搬迁,一砖一瓦地垒起来,脚手架林立着,叮叮当当的声响,白日黑夜地闹着,竟也一日日有了眉目。再后来,便有了宾川高平一中开班办学的人声,琅琅的读书声从新起的楼里飘出来,混着青草的气味,软软的,教人心里也跟着亮堂起来。我看着她,像看一个孩子,从蹒跚学步,到渐渐地挺直了腰杆,有了自己的气象。这十年里,她从起步到发展,一步步走来,而我呢,也从四十走到了五十。
 四十到五十,这其间的沧桑,是不必细说,也说不尽的。仿佛昨日还在为一些得失计较,心头总绷着一根弦;如今却像是站在秋日的河岸上,看着水静静地流,风凉凉地吹,心里头虽是明白那水底的石头与漩涡,却也懒得去指点议论了。
四十到五十,这其间的沧桑,是不必细说,也说不尽的。仿佛昨日还在为一些得失计较,心头总绷着一根弦;如今却像是站在秋日的河岸上,看着水静静地流,风凉凉地吹,心里头虽是明白那水底的石头与漩涡,却也懒得去指点议论了。
这十年间,因了工作的缘由,我的脚是走了不少地方的。
在永平县考察工作的时光里,第一次吃的黄焖鸡,是在一个傍着公路的小店里吃的。店堂里油油的烟气,混着辣子与姜蒜的焦香,直往鼻子里钻。那鸡肉是切得大块的,在浓厚的酱汁里炖得烂烂的,用白瓷碗盛着,油光锃亮。吃下去,身子便暖了,那一种踏实的可口,是专为慰藉旅人风尘的。这味道,如今想起来,舌尖上仿佛还留着一点余温,只是那店,那路,那日同坐的人,都模糊得像隔着一层毛玻璃了。
 还有洱源县的乳扇,那又是另一番光景。是在一个清净的院落里,阳光从照壁的一角斜斜地照下来,落在石板上,亮晃晃的。主人端上来的乳扇,白白净净的,像一片片卷起来的月光,带着一股子奶香的醇厚。吃起来是淡淡的甜,韧韧的,要慢慢地嚼,那香气才一丝丝地从齿缝间逸出来,教人不敢大声说话,生怕惊扰了这份安宁。这醇香,比起永平的浓烈,便显得格外清远,像是山间的一缕笛音,悠悠的,飘出去很远,却又抓它不住。
还有洱源县的乳扇,那又是另一番光景。是在一个清净的院落里,阳光从照壁的一角斜斜地照下来,落在石板上,亮晃晃的。主人端上来的乳扇,白白净净的,像一片片卷起来的月光,带着一股子奶香的醇厚。吃起来是淡淡的甜,韧韧的,要慢慢地嚼,那香气才一丝丝地从齿缝间逸出来,教人不敢大声说话,生怕惊扰了这份安宁。这醇香,比起永平的浓烈,便显得格外清远,像是山间的一缕笛音,悠悠的,飘出去很远,却又抓它不住。
 罗平县的油菜花,我是三月里见的。那真是一片海了,黄灿灿的,从脚下一直铺到天边去。风一过,那花浪便一层一层地涌过来,带着扑鼻的芬芳,甜得有些发腻,却又让人忍不住要深深地呼吸。人站在那花田里,便小得如一粒芥子,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了。这芬芳,是热闹的,是青春的,是扑啦啦一下子全给了你的,不像乳扇的香,要你静下心来去寻。
罗平县的油菜花,我是三月里见的。那真是一片海了,黄灿灿的,从脚下一直铺到天边去。风一过,那花浪便一层一层地涌过来,带着扑鼻的芬芳,甜得有些发腻,却又让人忍不住要深深地呼吸。人站在那花田里,便小得如一粒芥子,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了。这芬芳,是热闹的,是青春的,是扑啦啦一下子全给了你的,不像乳扇的香,要你静下心来去寻。
师宗县的菌子山,却是巍峨的。去时已是薄暮,山色成了墨绿,一层叠着一层,沉甸甸的,仿佛含着千百年的沉默。那山是那样地静,让你觉得自己的脚步声都是一种冒犯。我站在山脚下,仰头望着,心里便生出一种莫名的敬畏。这巍峨,与罗平花海的烂漫,是全然不同的;它什么也不说,却让你感到自己的那点愁烦,是何其的渺小了。
 我也曾考察过桐柏县的茶旅文化,看那些绿莹莹的茶树,如何被制成清冽的饮品;闻过宣威火腿那诱人的、经过时光熏烤的咸香;也曾在楚雄的古镇里,踏着青石板路,看那飞翘的檐角衬着蓝天,觉着一种说不出的、古老的浪漫。这些,都像是散落在路上的珠子,一颗颗,都曾被我小心地拾起,在掌中摩挲过,温热过。
我也曾考察过桐柏县的茶旅文化,看那些绿莹莹的茶树,如何被制成清冽的饮品;闻过宣威火腿那诱人的、经过时光熏烤的咸香;也曾在楚雄的古镇里,踏着青石板路,看那飞翘的檐角衬着蓝天,觉着一种说不出的、古老的浪漫。这些,都像是散落在路上的珠子,一颗颗,都曾被我小心地拾起,在掌中摩挲过,温热过。
 可如今细想起来,这一切,竟都成了过眼的烟云了。那些味道,那些颜色,那些气息,分明是那样真切地经历过,此刻却像退潮后的沙滩,只留下一片湿漉漉的痕迹,勾勒不出具体的形状了。我仿佛一个捡贝壳的孩子,在岁月的海滩上奔忙了许久,拾了满满的一怀,等到夕阳西下,低头一看,怀里却仍是空空的。这倒不是说那些经历没有价值,只是它们都沉到心底里去了,化成了我走路的步子,看人的眼神,成了我的一部分,再也分不开了。
可如今细想起来,这一切,竟都成了过眼的烟云了。那些味道,那些颜色,那些气息,分明是那样真切地经历过,此刻却像退潮后的沙滩,只留下一片湿漉漉的痕迹,勾勒不出具体的形状了。我仿佛一个捡贝壳的孩子,在岁月的海滩上奔忙了许久,拾了满满的一怀,等到夕阳西下,低头一看,怀里却仍是空空的。这倒不是说那些经历没有价值,只是它们都沉到心底里去了,化成了我走路的步子,看人的眼神,成了我的一部分,再也分不开了。
 窗外的光,愈发地淡了。十年,就这样从指缝里流走了。我陪着它,它也陪着我,我们都变了模样。那些走过的路,尝过的味,看过的山,如今都静静地卧在记忆里,像一本翻旧了的书,纸页泛了黄,字迹却还依稀可辨。我合上书,心里并无多少悲伤,也无多少欢喜,只是平平的,淡淡的,像这欲暮未暮的天色。
窗外的光,愈发地淡了。十年,就这样从指缝里流走了。我陪着它,它也陪着我,我们都变了模样。那些走过的路,尝过的味,看过的山,如今都静静地卧在记忆里,像一本翻旧了的书,纸页泛了黄,字迹却还依稀可辨。我合上书,心里并无多少悲伤,也无多少欢喜,只是平平的,淡淡的,像这欲暮未暮的天色。
也好,这样也好。
作者/李红文
编辑/杨宏毅
责编/杨宏毅
审稿/张进
终审/杨凤云
投稿/bcrmtzx@163.com


网友评论文明上网,理性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