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节日·春节】年来米花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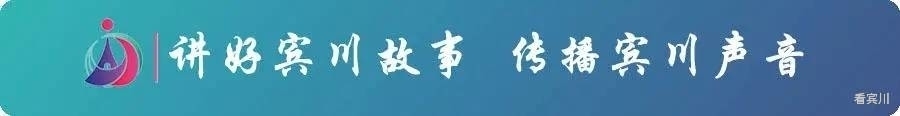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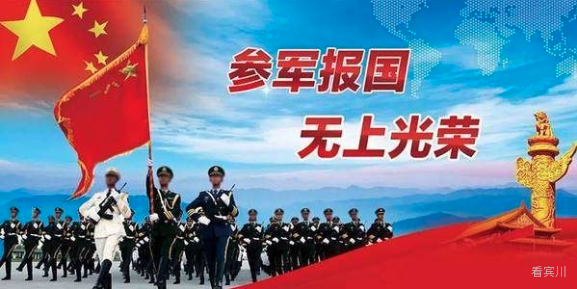

我的家乡宾川曾经盛产稻米,人民的生活也离不开稻米,而那些幸福快乐的日子,却与又香又软的糯米密不可分。因为有了糯米,平凡的生活就变得香甜软糯,幸福美好多了。

儿时,每每年关将至,母亲就会用米筛将碾好的糯米筛一遍,筛下去的糯米被淘洗浸泡之后,就被磨成了糯米面,这是过年时候必不可少的东西。而留在米筛上面的整颗的大粒的糯米,母亲把它们淘洗泡透之后,就用甑子蒸,一甑子又一甑子地蒸,真香啊,一家蒸糯米,满村都飘香!而蒸糯米的时候,每一甑子都不能多蒸,蒸出来的糯米,倒在竹簸箕里晾着,又香又软的糯米饭,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我们一团团的抓了放在嘴里,不加糖很香,加了糖又甜又香,那叫一个好吃啊!
糯米饭晾在簸箕里,由热到凉,由软到硬,由大块渐渐地散成了小块,最后,变成了一粒粒的米,在这个过程中,米粒一天太阳都不能晒,必须一直晾着,晾干为止。这样制作出来的米粒,叫做阴米。


到了过年前几天,街上钟鼓楼下面一溜地摆开了许多的土坯灶,灶上的大锅里,炒着油亮的沙子,热热的沙子里,就可以炒米花!细细的泛着油光的阴米放进热沙里,三炒两炒,阴米华丽变身,成为了白白胖胖的米花,抓一把,放在嘴里,一嚼,“嚓嚓嚓”地脆响,又香,真好吃啊!


除了炒米花,还要炒红薯干,炒花生,炒葵花籽,炒瓜子,炒豆子,过年嘛,就是要吃香的,喝辣的!而这些,都是自家田里地里种出来的,好吃而且绿色环保!
那时的春节,很有仪式感,也年味十足!


大年三十的中午,父亲带着我们,用一个盆将煮好的腊猪头盛放好,用筷子撑得饱饱满满的;用一个盘子将煮好的整鸡,也用筷子撑起盛放好,嘴里衔上一朵鲜花,要么是早开的山茶花、要么是早开的桃花;再用一个盆盛放猪脚、猪尾巴、一块方形的五花肉;再用一个盘子,摆上新鲜的三菜三饭,三双筷子,一家几个人恭恭敬敬地端到一里地之外的土主庙,恭恭敬敬地敬献,回来后,才在家里敬献祖宗!年年如此!


零星的火炮,整天响个不停,吃饭时候,一串串的火炮声便此起彼伏!大年初一的大清早,将炒回家的米花,放在碗里,上面盖上切好的红糖,用刚烧开的开水一冲,一碗又香又甜的米花开水就冲好了。我们就吃这个,家家如此!来客了也先吃这个,家家如此!只是我们吃米花的时候,要挑上一坨猪化油,母亲说烫米花时放上猪油,吃了不上火,这样吃,不流鼻血,不咳嗽!

吃完米花,喂好猪鸡牛,孩子们就会提着用米花做的五颜六色的圆圆糖,衣兜里揣着煮好的红鸡蛋,裤兜里揣着压岁钱,高高兴兴地逛街去!
观音阁唱大戏,滇戏典雅,可是有些难以看懂;花灯通俗,且能够紧跟时代步伐,所以成为了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整个正月,花灯团就演了一场又一场,场场爆满!我们挤在人群中,开心地笑着,看着,开心极了!

那样的日子,已经无法重来了!一来岁月倥偬,转眼之间,红颜已老,青春不再,满头的青丝渐渐变成了白发,而当年为我们炒米花的母亲,早已辞世!二来物换星移,故乡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故乡,房屋变了,街道变了,田间种植的农作物,已经不再以稻米为主,兼种五谷杂粮了,而是一片片的葡萄,间杂以一园园的石榴,柑橘、枇杷……农民再也无需春种、夏耘、秋收、冬藏!我已经很久没有闻见稻花飘香,没有听见蛙鸣虫唱,没有吃到新米饭、新糯米饭了!而且生活习俗也随之变化,年俗也一变再变,到如今,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事情,是过年的时候必须做的、或者是过年时候一定不能做的了!只有压岁的红包,一年比一年大!
文/熊剑虹(转自《宾川与文学》)
图/杨宏毅
编辑/杨宏毅
审稿/朱晓天
终审/杨凤云 刘灿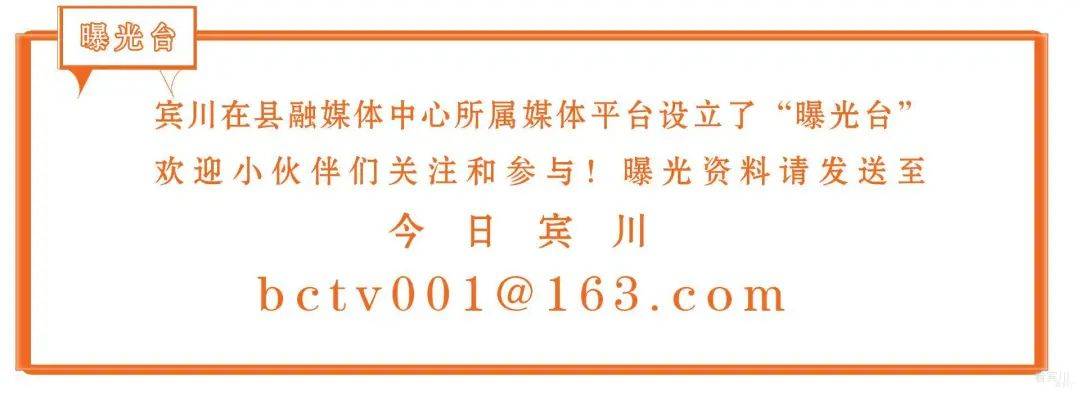



网友评论文明上网,理性发言